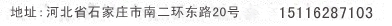梦柯老村完整篇
老村
村里人都喜欢称村子叫老村。
那个小老村,你说悠久历史算不上,不过据说爷爷就是从那里跟国民党部队走的。
村子不大且分南庄和北庄,那条通往城里如银蛇一样的路就在南庄,杨杏喜欢去南庄路上玩。她家住北庄。北庄有杨树、楝树、狗棒椿树,枣树、榆树、桑葚树,洋槐树、石榴树、梧桐树......再往北庄的最边上走有一条小河,小河常年缓缓流水,偶尔有小鱼。
杨杏是女孩,她不敢下水,一只蚂蝗能把她吓个半死。她不喜欢北庄到了冬天满地黄叶继而变成黑叶子的腐朽苍凉,夏天的庇荫葱茏,还有知了,秋蝉,树上袅婷的各色小鸟等挠不起杨杏的兴趣,她偏偏喜欢去南庄的路上看有人骑着自行车路过,还有马车通过,拉马车的不是马,大多是驴子。
杨杏看驴脖子上搭的那个东西很好看,驴也很听话,嘣嘎,嘣嘎从眼前消失,杨杏更喜欢看偶尔过来的大汽车从银蛇一样明光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母亲大声叫喊她回家拾柴,填灶火,她很不耐烦。上边还有几个姐姐下边唯一的一个小弟弟为什么不叫她们,她一边看那条光闪闪的路,一边愤恨她母亲叫她,好像又一辆汽车过来,她只是看看,她一直喜欢看看,自行车过的也不是很多,她想有一天能骑上自行车像那些姑娘媳妇们还是男劳力们自由的转起那两个轮子的东西该有多么欢畅。
她只是欢畅的想而且想了很多,从南庄回到北庄,不远,路不是直线需绕过王国良家又绕过张凤普家,最后绕过她伯伯家才能到她家。她家周围的大树遮住了房子的模样,房子是三间瓦房,院子里放的是耕作农田用的牛笼嘴,木锨,铁叉,犁铧,挨着房门外是一个玉米杆搭的牛棚,还有两头牛。杨杏家的主要家业应该是那两头牛,她老爹老骂她母亲肚子长邪气了只会生丫头不生带巴的,五十岁才生了她小弟,农忙活全是几个丫头上去干的,她老爹说谁让没劳力,活该!
她听到老爹说的话极为嫌烦,比屁还臭,她不想看她爹,从地里回来像佛祖一样被她老妈恭敬着,她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就是不想和她老爹一起呆着。
每次看完汽车,自行车,马车回来睡不着觉,那条银蛇一样的路到底能通向哪里?她想知道,她觉得那是一种引力,吸引着她强烈的思神向往。
她的欲望被老爹打死后暴晒的阳光下,老爹让她上田里干活,掰玉米,一大片的玉米,她几个姐姐当然一个也少不了,她小弟赛皇上似的在家吃老妈炖的鸡蛋糕。
她说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这么不一样,她长很大还在重复这句话,男娃娃和女娃娃不一样,不知道怎么不一样,反正就是不一样。
看她老爹是乜斜着眼看的,特别老爹用一把烟叶摁到烟袋锅里,火柴划着点燃后,兹兹拉拉抽蹦响时老妈把一大碗捞面条端上来,他立马磕掉烟灰扔了烟袋又是一翻哧溜溜的声响,她发誓不跟他,她几个姐姐也吃的呼呼啦啦,地里干活饿的吧,蒜面条吃起来真香呀,蒜面条也是分了顿吃的,她家是面少人多,收回来的常常不够吃,另外要红薯面贴补,玉米面搭配,蒜面条是特地给她爹和小弟开小灶,五个姐姐和她均没有份,有份也是偶尔,干的活是累死人的活才肯让吃上一顿蒜面条,譬如出大粪,牛粪上地里,一辆木车我们叫“架子车”一车又一车的拉到村庄四面八方的地块去,还要一点一点用铁锨豁开伴匀实,她老妈更不用说,她说的什么老妈和姐姐们根本就不理会。
她喜欢一个人玩。
玩的没滋没味时就看自家屋檐上飞来的鸽子,灰白的,白色的,黑色的,那些鸽子偷吃她家玉米,麦粒,她老妈碰到就打,她起来夺了老妈的扫帚气狠狠的说鸽子会说话。
她老妈就会骂她一句:“狗屁”
杨杏想跟老爹去公社开会,她老爹不让去还骂她:“一个妮片子家疯跑什么给我好好的呆家里跟你姐们上地干活.......”她固执的跟老爹身后,老爹回过头脱了黑布鞋打了她几下,她没去成哭着回家了,老妈又跟上一顿骂:“死闺女的,你爹人家是劳力,你个妮片子去干啥呢?”
她想去,想看公社什么样的,人们开会什么样的,她更想知道她老爹去了会干些什么,她都在想,这些小想法折磨得她眼神好没光气,只好傻呆呆的看老妈纳鞋底做鞋帮。她老妈把一根根合股的线用陀螺扎一根筷子搁成绳子,若没鞋帮了就从墙上取下来一块略微厚一点的(quezi,这个字我不会写,只好用拼音代替。),其实是碎布块和面糊合成的那种东西,母亲三下五去二用一把黑剪子就剪出一个个鞋帮来,有她几个姐姐,老爹,还有小弟,当然也有她的。她老妈做鞋子一个不能少,几个姐姐们老抱怨老妈用黑鞋帮,她们想要那种灯芯绒的彩颜色布面做鞋帮,好看,老妈就会说出一句至关紧要的话来:“钱呢?”
是真的。她老妈说“钱呢?”
的确她家没有钱,平时吃的都显得紧张,哪有钱买彩面灯芯绒?她的姐姐们也真能要得出口,姐姐穿什么她也穿什么,家里除了牛值钱但要犁地用,绝不是卖品,更不说那几个鸡子留着它们下蛋给小弟吃,老妈坚决舍不得卖,是公鸡长大一点给她老爹补亏吃了。她老妈总说她爹亏,老妈从来不吃,杨杏长这么大也没有见过老妈和老爹抢吃那炖熟的老公鸡,她就更没有份了,姐姐们靠边站,小弟吃着还闹人,杨杏就想揍死小弟,一万个为什么在她心里反复粘缠。
这都是老村里杨杏每天都要过一遍的情景。
她不愿意回顾,只有到了南庄的路上,她感觉心里不会有北庄那棵棵大树的遮盖,天空是透彻的,绚烂的,她依旧仔细的看那条银蛇的路从她跟前走,再继续走,走到哪里也许比跟着老妈,老爹强,她纵横的盘算她什么时候能够骑上自行车像路上自由的人一样,来去自由。
她大姐被一个说媒的很快找人家出嫁了,那个男人来她家,不见他说过什么话,村上人说她大姐嫁了一个哑巴,她大姐生孩子那年总算听到她姐夫费了很大劲说她老妈:“大妮生了。”
“她生了,你来找我干嘛?”
“那,那,大妮是难产,孩子先出来的脚,不是头,大妮叫的不行。”
“你个笨蛋的,去找接生婆呀。”
“她叫的声音,怕是快死了。”
“滚。”
“......”
杨杏听见老妈和姐夫在因为姐姐生孩子的事被老妈骂,才知道姐夫是一个没多大能耐地里活也干的不夯实,对家里所有的事情一点提不上公堂的笨蛋男人,难怪老妈骂,谁让这家女多男少呢,再说她姐姐长的也不怎么好,一副宽大如劳力的身子外,找不出像女人的地方,她很害怕姐姐生孩子死掉,她第一次耳朵这么近的聆听死亡,她感觉恐惧,虽然不懂生孩子,但她有种说不来的害怕。
她老妈不轻不重的说她也跑不过那一关,生孩子,那个女人都别想跑掉。
她不敢想了,她一直还去南庄看银蛇,看云,看天,看燕子飞来飞去,看自己的心情被蓝天勾走,被汽车拉走,被自行车拽走,她很久没有去她家的后边,那些参天的大树一到晚上带着风的哨子,呼啦啦作响,她睡在房内都能听见,她不喜欢,她有一种无助的害怕。
那年她十五岁。
老爹回来说公社大院很气派,办公,干事,开会的,那些当官的就是和咱老百姓不一样。大院里还停一辆北京吉普车呢,那真是公社大院呀,当官的一座到主席台上,地上坐的社员们没有人敢说话,要新派一批驻队干部下来,具体她老爹说不清,只知道分干部驻队,杨杏公社没有去过,老村大队院是去过的,一溜烟排开的瓦房,大队院还算干净,在杨杏的心里那是和老百姓住的房子不一样,平常家的老百姓哪家不养几只鸡,一头猪,几只羊子?杨杏家养的两头牛就很显摆了,她老妈说那两头牛是他爹的命根子,出大力的干将,要一群妮片子们也不见指望得上。她老爹看那两头牛比看她的几个姐姐都重要,几个姐姐在家出牛粪,到地里站耙,杨杏伯伯曾说她的几个姐姐个个赛似老铁驴,老铁驴杨杏没有见过,她伯伯见过,什么样的呢?
她又想了好久没有想出来,老铁驴什么样子,不过有一点她是明白的,她姐姐们都很能干,除了大姐杨丽萍出嫁外,二姐杨丽华23岁,三姐杨丽娟21岁,四姐杨丽梅19岁,她16岁。
新来的驻队干部就住在大队院瓦房里时,已是老爹去公社开过会的2年后。
村里开会表示欢迎这些新干部,杨杏和她老妈,几个姐姐都去,那次她老爹没有管,社员们都去了,整个大队院子全是人,老村的39户人家没有不到的。
杨杏很欢欣,她的三姐更是欢欣,她看到主席台上坐的几个年轻男干部,她没有去注意过姐姐的表情,姐姐一下子就看上其中一个叫罗震东的,杨杏看的不太明白,也能有一点含羞的梅花落韵感,她也看过姐姐一直盯着看那个男干部,她也看了几眼,谁知那个男干部也看了人群里显眼的几个姐妹,有她和她三姐。
会开完了,杨杏走路的步子慢了点,那曾想三姐的步子更加的慢,还不时回过头看已经散场的主席台,主席台上有村支书在忙收拾茶瓶,茶杯,那个年轻的男干部已经在这边晃动着身体和其他几个说的什么,她们听不到的,也只这么回头看了。
回家老爹像展演节目一样把开会的内容唠叨一遍说:“这下可好了,日子就有好过的,来的人都是农业技术员呢帮咱们管理田地。”
“管又咋地?咱难道就不干活了?不管咱还不是要干活?”
“你懂个屁啊,真是妇道人家。”
“他们来管了,你就真不干活了?”
“不是,村长老敦要下,我想干村长。”
“嗯,地黄瓜还想爬上金陵屋?”
“你就看着吧。”
“呵呵,那你就逞能吧。”
“......”杨杏没成想过她老爹还想当村长,她想的却不是这些的,白天会场主席台上的那个年轻男干部罗震东她忍不住脸红,又想了一遍再想了一遍,灯吹灭了,眼儿瞪的依旧圆鼓,比她去看南庄那条银蛇一样的路要美好的多,温润的多,那个男干部也看了她一眼。
她并不知道那个年轻的男干部叫罗震东,标准的一个城里人,清瘦文静带一副眼镜真像老师,她三姐和其他女子们一起说笑时她知道他的名字的,她三姐就敢说,她老妈骂过她三姐是疯狗,那么着急出嫁,在家里干几年觉得亏,是不?到婆家不干活,不纳鞋底子做棉衣总是不行的,她三姐只有在她老爹不在时顶撞她老妈几句:“你还想让我在家长多大呢,长成老妮可是没男人要的,丢人还不是你丢人呀。”
她老妈就没话了,她三姐生的伶俐聪慧,比大姐,二姐,四姐标致,放人堆里是那种招惹眼的女子,每天看姐姐们挤着一个镜子看眼睛又是弄鼻子的杨杏觉得烦,她不是不喜欢看,她觉得几个姐姐有时候为争那个镜子还要吵架呢,老爹在堂屋听见就骂开了:“没看都长的破棉花桃子似的看个啥?”杨杏每次等姐姐们看过后才偷偷的拿起那个红塑边的圆镜看自己,镜子里的自己敢和三姐相比了,三姐一双大眼,她也一双大眼,三姐一副高鼻梁,她也一副高鼻梁,姐姐一头长发,她也一样的拥有两个又粗又长的黑辫子,在杨家只有她和三姐是人尖儿,老妈总是使劲的按下去,故意让她们穿的更寒碜,一个露着棉花的袄子被一件又大又难看的灰蓝色对襟上衣遮盖,夏天来了,更甭想南庄银蛇路上穿裙子走来走去的女子,杨杏那刻就有一种很深的失落,枯败的情绪萦绕。
她老爹又去大队院开会了,自从老爹去公社她要跟那次挨过打后再也不跟老爹去哪里了,老爹一直想干那个村长了,回来没少听到他唠叨,她老妈总是撇撇嘴说她老爹赖蛤蟆想吃龙肉想疯了,老爹不以为然老妈的话,早早喂好了牛去大队院,那群年轻的男干部真招眼,在村里一晃都有一种和村里人绝然不一样的东西,那叫“文质彬彬”的气质,这个词杨杏只是听人说过,怎么写她不会写的,她没有读过书,几个姐姐更不用说都没进过学校的门,老村是没有学校的,离老村三公里外的街上有所学校,那是中学和小学并用的一所学校,杨杏怎么着想去上学,老爹老妈的共同意见是:妮片子家读书也是给婆家读的,到了婆家还不是照样生孩子,干农活?”
杨杏背地里骂过她老爹不是东西,老妈不是人,当然她骂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呆着玩的,她第一次去了北庄她家房后的那条小河边上,看小河里的小鱼儿那么自由的摆动身子,青草,浮萍什么的,她看完后忍不住哭一阵,鱼儿为什么那么的自由而自己每天为什么这么难受,她看一眼的年轻男干部,她三姐也在看,她三姐居然公开叫那个男干部的名字,她不敢叫,只偷偷的想一遍又一遍,那个年轻男干部会再看她一眼吗?
她老妈叫她吃饭的声音很大,有一种羞辱感,这么大的闺女还挨骂:“你个死闺女的,偷鸡养汉了嘛,怎么喊不答应哩?”
她心头立刻一股烈火窜上来,恨不得掐死她老妈,说她老爹的话难听,说她几个姐姐的话更难听,对她也同样,她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记事以来看见老妈就这样,长大老妈依旧这样,老爹从来就没有变那个样子,整天想和大队院里某些人挂上,自家没面借面也要让老敦来吃饭,杨杏从没有想过老爹竟还阴分着呢,表面上叫老敦一个大哥长两个大哥短的,背地里一直想整掉老敦村长的职务,她不知道老爹整天都是怎么想的,干个村长有什么好的呢?能多收几担粮食还是能多拿几文钱?从她老爹想干村长这件事情上,老妈的态度不是很支持,老说老爹不正道,干个村长也是个整人的坏东西。老爹就会来一句结尾话:“你们懂个屁。”
杨杏从来就没有弄懂她老爹,老妈就更不用说了,五十岁领个带巴的小子在老爹面前说话仗势,气长的,老爹再也不说老妈的肚子长的邪气了。
要打棉花顶了,老爹一股烟叶味的叫喊她们姊妹几个赶快上地,十几亩的地不抓紧打顶那棉花疯长成渐枝影响坐桃子,杨杏就跟上几个姐姐一前一后去地了。
干到半晌里觉知地那头有一群人,杨杏回过头看,几个姐姐也把头扭过去看,她看见了,那个戴眼镜的男干部罗震东的,还有另几个是大队院开会时主席台上并排坐的人,那几个也一样的年轻,只是都没有罗震东更有俊秀的气质,人家是城里人,竟然愿意下来当农业技术员?
杨杏没有想的那么深远,她只是觉得这个村子太不衬这些人的存在了,但他们的到来就是给杨杏一个别样的说法,一切都可以存在,城市的,农村的,农村的,城市的,她想起那条银蛇亮白的路来,他们断然知道那条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那几个人跟着老爹屁股后一点点向她靠近,她的两只小手摸着棉花顶不由的颤抖,惊悸,手心里很快湿润,脸上也一阵火辣,心儿里活像装了数十只兔子跳来跳去,只听见老爹说:王技术员,这是我今年种植的小叶棉,这个是头一年种植,还不知道怎么打理,你们来了,可不愁技术上不懂了。”
“小叶棉前二年都推广了,只是到你们这个地方有点晚,成活率相当高,坐桃率也不错,好好管理要比以前的大棵棉收成好,大棵棉很容易疯长,如果控制不好那能长成一棵棵小树还不结桃子,所以现在上边让推广这个,棉花棵比较低矮,接受光照强,棉花的成色也亮彩的。”罗震东很文雅的说给老爹。
“那是,那是,要不让你们下来呢,真是我们的救星啊。”她老爹几乎把头都凑到罗技术员的鼻子尖上。
“该打农药时,一定要打的,不要怕浪费小钱,就是没有虫子也要预防,预防为主的。”王技术员补充给老爹。
“.....”
杨杏不想再听见老爹说话了,他们几个说话,杨杏想听到只是跑垄沟错开了,就听不到了,又看一看罗震东穿一件白色衬衣,下穿深蓝色裤子,那裤子很好看的样子,正整洁,不倒褶,其他几个也一样的清爽,这就是农村和城市人不一样的地方。
农村人总是穿的灰土土的,她老妈回趟娘家还接东家二婶一件上衣和一双皮鞋,老妈说回来是拎着皮鞋回来的,皮鞋太小,她脚太大,挤脚,疼的走不成,老妈因为这个很少回娘家的,外婆家也没有人了,回家顶多是给她哥嫂,兄弟们摆谱的,她也曾经说过男人要干村长了,家里人都为老妈填上一堆好话的,老妈满意十足的回来,那次借衣服,鞋子的事情被老爹骂了:“瞎摆弄个啥?那黑老布鞋就穿不成了吗?我看穿着怪美气的,你们女人尽瞎愣愣。”老妈占着小弟的威力也骂了老爹:“看你那老不死的样子好啊,谁像你,干个村长就恨不得把自己庙堂陪上,呸!”
那几个人又和杨杏走的很近,又一条垄沟中间,他们跟着老爹走到了地中央,她悄悄的乜斜眼低头看那个罗震东的,那个罗震东怎么一直在看三姐,老爹说的什么话,他似乎不再接了,只顾看三姐,她心里好酸,好沉,好难过,她想让他也看自己一下,那几个人不同目光的看过她,她也看到了,只是罗震东没有看她,立刻不想在打下去了,她老爹还在那里瞎说,她想这样也好,她那会更想让老爹狠劲的说,努力的说,说的中午别回大队院吃饭,在她家吃饭才是好的呢,那老妈又该骂了,又一次把庙陪上的。她不管,她希望是这样的。
太阳很毒辣了,汗水把衬衫打湿透贴到皮肤上,小背心兜着两只鲜亮的小乳房显得几分羞涩,几分难堪,她们只干了几个垄沟,太热了,几个姐姐吵了老爹要回去,老妈接着骂她们吃嘴不下力的货都给接着干,这时三姐打头说了,中暑了,赶明个一垄沟也干不来哪划算?”
“那你们就回吧,大瓢挖面,三瓢,压面条吧,我回去炒菜,这些人你老爹说中午在咱家吃饭呢。”
“好滴。”
几个姐姐跑的可快了,三姐最后一个走,杨杏明白三姐的意思,是多想看一眼那个罗技术员,其实谁又不是呢?
那顿饭吃的很欢实,几个年轻人大概是很少吃到这样的饭,蒜面条,外加几个菜,母亲能凑菜,晒的红薯叶也是一道菜,干豆角拿出来也是一道菜,鸡蛋煎饼也是一道菜,粉条放锅里煮了,出来也用蒜泥拌了是一道菜,那几个人看谁吃的嗤啦啦的响,她老爹吃的没脸没皮,吃一碗喊叫她老妈再来一碗,其实她老妈那天中午没吃上,是面条不够吃,菜是给客人吃的,她吃了早上篦子上剩下的玉米馒头,粗砂一样嚼在口中的感觉,杨杏吃的只想吐了。
可是吃了一顿又一顿,不吃肚子饿,吃了又实在的厌烦。
她越来越鄙视她老爹,只是那天中午她觉得老爹是那么的可爱,把她想看的人能带到自己家里,她愿意把自己的那碗蒜面条省出来给他们吃,也许她更希望罗震东吃了。
罗震东终于上下仔细的打量了一下杨杏说:“这姑娘定是干活的好手吧,挺伶俐的。”
“再伶俐也是丫头片子,不当劳力用。”
“大叔,可不要这样说的,我们城里的女人一样上班的,有的比男人还顶用呢。”
“这是乡下,没办法,乡下的女人是没有多少用的。”
“大叔,说话见怪了。”
“......”
杨杏和三姐听的心花怒放,其他几个也看了看二姐,四姐,目光驻留的应该是她和三姐,三姐那天中午是出尽了风头,一会端菜,一会端碗的,那个罗震东的看了一遍又一遍三姐的,那根粗粗的马尾辫一会前一会后的,甩来甩去的煞是好看,她也觉得三姐真的很好看,难怪那些年轻的男干部没有一个不喜欢看的,看她的也是很热烈的,她没有三姐胆子大,那顿饭吃完后她偷偷的去过大队院,还有明着去的,明着去是找她老爹在不在那里,那个罗震东和三姐已经有话说了,她那晚出去找小弟看见的,罗震东和三姐在大队院的西山墙那里站着,为什么老爹就不骂了呢,老妈就不管了呢?
她觉得很委屈,找回小弟她就睡了,她没有睡,哭的泪人似的。
她开始恨那条因蛇一样的路了,特别是下雨天更加的恨,下雨天的人们都没事,不是挤到一起说闲话就是打牌,赌博在老村已经有些年头了,当然她老爹也赌,赌的惨重那会输掉一布袋小麦,她老妈骂死了,再遇赌场不敢上了。而这时的下雨天那些技术员们也不干什么事情,尽吃吧,玩吧,三姐没有事没事就偷跑出去和罗震东闲谈去了,她不明白一个事儿是她老爹老妈竟对她三姐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意思呢?
大概是老爹老妈也看上那小子了,看那小子也看上自家闺女了,一件喜欢的事怎么能说闺女败坏门风?
他们默认的事,所以三姐才那么胆子大。
她好后悔自己为什么胆子小呢?罗震东不只是看过三姐,也看过她几眼。
纠结,杨杏她怎么会知道这个后来派生的词呢,纠结,真是好纠结。
她眼儿瞪的杏子一样看罗震东把三姐杨丽娟带走了,从那条银蛇一样的路上轻盈的走过,三姐那天起的特别早,穿了母亲特地去街上扯的红底碎花布做的偏襟上衣,下穿一条崭新的蓝裤子,走的时候还摸摸杨杏的头矫情的叫了一句“可要听咱妈的话,不许胡闹。”
杨杏一股怒火,却又不知道怎么发出来。她憋的难受。
不知道心里想的什么,那会看见罗震东,罗震东也那么回过头再次看他一眼,那一眼,温柔!厚重,甜蜜!为什么不是和杨杏呢?
她知道罗震东只顾牵了三姐的肩膀在这个只有39户人家的村子里走来走去,他老爹又该怎的背地里骂死三姐?老爹不但没有骂,还挺欢喜!
杨杏很委屈又巨大的悲痛,愤恨!
她眼巴巴的看着三姐和罗震东那样的牵着,还大摇大摆的走在她一直喜欢的南庄那条银蛇路上。
三姐走上南庄的路上,那路上立刻堆满了人,那几个驻队小年轻干部也来了,还有村上的那些男女老少,都说杨家三闺女摊上好福气了,能跟了罗技术员真不了不得,三姐那天的脸上像春天开满院的桃花一样,肆意的绽放,杨杏飞快从南庄的银蛇路上跑回家,一头扎进被子里嚎啕大哭,她的哭声是否惊动房后大树上的飞鸟?还是惊动屋檐下的白鸽子,黑鸽子,灰鸽子,她不管,她要哭出来,她要委屈出来,反正这回老爹,老妈都去南庄的路上,看罗震东带三姐走,老妈竟然还让三姐拿了两只鸡,说是给罗震东的城里父母吃,拿两只鸡叫的特别响亮,罗震东几次欲说要杨丽娟放了那几只鸡,一会走上公路乘坐票车就麻烦了,杨丽娟却很坚持,他们走了,走了很远的地方时,杨杏的老爹老妈才慢慢走回去,村上人这个叫老杨你这下可有福气了,那个说闺女遇到个城里人,真是好命啊。
杨杏老爹就会笑的眼儿迷成一条缝儿,他怎么不希望自家闺女嫁个好人家呢?这不,还真是遇上了呢,所以他没有管杨丽娟三女儿那么严厉,罗震东三天两头往他家跑,今天拿来一个口琴,明天拿点杨丽娟没有吃过的糖块,杨丽娟经常和她几个姐姐说城里这个好那个好的,几个姐姐听烦了就说你嫁到月球上俺也不稀罕,少给俺们啰嗦的。
杨杏的三姐就不敢再说了。
杨杏倒想听的仔细,她想听到更多关于罗震东的事儿,那几个技术员长的也不错,气质也有可杨杏怎么看也没有罗震东让她看着眼红心跳,极度愁绪,又陷入神经上的无限抽搐。
她不懂,那叫爱情,她爱上了这个年轻的驻队干部,令人沮丧的是她三姐也爱上了他,她哭了很久,天快黑了下来,牛棚里的牛在那里嗷嗷大叫,老爹还没有回来拌草料喂它们,每次老爹拌草料都要杨杏捡出来里边的杂质,特别是怕牛吃了铁丝,铁钉等之类的东西,能把牛吃死,她老爹说,她就烦。
她希望老爹不要说话。
她自己什么话也不想说的,三姐这个时候应该和罗震东坐上去城里的车了吧?!
老爹忙着当村长的事情,听老妈说还真忙出了些眉目,他老爹很快就要干村长了,很快就要走在村上显摆他牛逼的神气了,老敦怎么能不知道老爹想干这个村长快想疯了,老敦也许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他怎么还隔三差五的来他家吃饭呢?
她老爹真不要脸。
背后阴的像驴,阴沉的简直比快下雨的天还要阴森,她很快服气老爹的做法,老爹拿出最后一袋麦子磨了面,让老妈蒸上几锅白馒头给驻队干部,还有乡里来检查的当官的,他真弄成了,快上任了,老爹。
她对老爹干村长的事情,一点也没有思想过,只是老爹喂两头老牛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殷勤,他居然把母亲也驯服的会喂牛了,只是那两头牛还真认人,开始不吃老妈下的料,老爹说慢慢就好了,果然过了没有几天功夫也吃老妈下的草料了。
这东西,也会懂得看上谁,看不上谁,那牛就没有看上母亲。
老爹真该是一个人才。
她哭完了想很多,窗外的月光很皎洁,银盘似的凝眉扰心,三姐是否到了城里吧,是否到了罗震东的家?她还在想这没用的事情。
想着不知不觉睡去了。
梦里,罗震东扒了她的外衣,再猛甩了她的红兜肚,露出两只圆鼓鼓的小小奶子,罗震东的舌头绕来绕去在她的口中,不大工夫杨杏晕厥,瘫软下来,梦里那么的优柔,酥润,潮湿,翻滚.....
二姐叫她起来,是老爹开会去了,老爹干村长上任的第一天,她母亲第一次说去看不?杨杏没有去,大姐抱着孩子也回来了,看老爹怎么当村长,孩子闹人,两岁还不会走路,大姐说孩子被人算过卦,会走的,只是摊上大富大贵的命所以走的要晚些,不着急。
杨杏想笑大姐,四十刚出头却和老妈一样的显老,那个男人真是个不成器的男人,干个什么事情都要大姐去干,去讨要,去办哪些长长短短的事情,大姐真是可怜,三姐摊上好运气了。
杨杏自然想不起自己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老爹老妈会给自己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她很迷茫,也极度料峭的想自己无知的未来。“快去,妮子们,捉只鸡来,咱们今天炖鸡吃,你老爹我今个儿心情高兴,咱村里的人不仅归我管了,地也归我管了,今年赶上大动地,咱们找几块好的留下来,剩下的让他们抓阄去吧,不愁咱没有好日子过的,快去.....”
“当个臭村长,就美成那样?!”老妈说老爹。
“可不,这是我想了多久才想到手的,咋么,你们不高兴吗?”
“哼,我们那有什么高兴的,还不是照样下地干活,吃几顿饭?”
“说你们真是妇道人家,你们还真是的,等咱福儿长大了,好接老爹的班,也干上个村长来。”
“呸,福儿长大了,说不定没准当个国家干部里?”
“哈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你还想那门子美事?”
“别这样说的。”
“你就瞎楞楞吧。”
“......”
杨杏听着听着不想再听了,起身去了南庄那条透着一种晶莹亮光的银蛇路,可今天却像雨天一样阴沉的说不出自己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她依旧想哭,看着夕阳的天红润的晚霞照过来,心里无限的落寞,伤怀,寂寞,她怎能懂什么是寂寞,可她却知道喜欢一个人呢,摸着心口,心口是疼痛的.......
杨杏三姐从城里回来全村人说这闺女变洋气了,浑身散发城里人的劲儿,先是头发烫的像拨浪鼓似的走起路头上的拨浪鼓经风轻轻那么一吹一漾一漾的,上衣由土灰蓝改了蝙蝠衫外套,裤子印儿笔直笔直的,衬的三姐俨然一个美人胚子可羡煞了杨杏儿,村里几个妇女骂杨丽娟个浪八圈的臭不要脸货,没几天可跟上野汉子跑了,那杨老汉也不管管自家闺女出去当破鞋?
杨杏听过几个妇女骂三姐的话没有多大的气愤,反而还有几分洋洋得意的给那几个妇女一脸的轻蔑,咋地?你们也想让人带你们上城里,一边等着去,也不瞧瞧你们那歪揣疙瘩梨的模样!
杨杏看见三姐回来给老爹买了一双运动鞋子,给老妈买一件料子比较柔软的衬衫,还给杨杏带回来一个小巧精致的头花就没有二姐的,四姐的,二姐没有觉得什么,四姐嘟囔着小嘴说都是姊妹的还挑拣个好坏来对地?
“没买就没买,嘟囔什么呢?”老妈满不在乎的说四姐。
“她也太偏向了,赶明俺也去城里。”杨杏四姐气呼呼的说杨杏的老妈。
“就你们女人们事多,出去吵去!?”老爹抢了二四姐的话说。
“走就走,谁稀罕跟着你们过呢?”四姐对着老爹干起仗了。
“你不想要脸了就走,没人拦你。”
“那三姐她干的事情难道就是要脸的事情吗,你咋不说她呢,让咱村里的刑二奶快把三姐骂死了。”
“谁爱骂就骂,我闺女找的是国家干部,撑死他们骂的。”
“哼,赶明个人家国家干部娶她不娶她过门还不好说呢。”
“那你就不要管了,管着给你找个人家让你出嫁就得了。”
“我的事儿也不要你们管,我自己找。”
“有本事,你就给我找个骡子,马的拉出来给我遛遛!?”
“还没见过你这样的爹。”
“谁家的爹好了,你就跟人家好了,少在这里发撒。”
“......”
杨杏见老爹和四姐你一句我一句的干架心里发慌又添堵的,老爹怎么能这么骂四姐呢?老妈一边白着眼不吭气让杨杏好气愤!自家闺女出去被人骂回来还要被自己人骂让杨杏很是难过。她去了南庄那条银蛇的路上,见老村长老敦一步浅一步深的抽着旱烟袋,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地里的庄稼苗,若有所思又几分迷惑,老爹挤了他的村长位子这多少让杨杏心里替老敦难过,老敦干的好好的被老爹这样一式子那样一整的,老敦的村长自然就卸任了,不过年52岁的老敦也不亏,干村长的那些年没少往家捞东西,队里的面布袋,大杆秤,爬犁了,木锨了,铁叉了都不是他自己置办的,动地时给自己找的都是上好的肥地块,河边有树的地块总是分给那些“猪无能”的人家,照老爹的话说:“你以为老敦是个好鸟,那也是牲口一个,整死他也不亏!”
杨杏看老敦走过去,另一个妙龄女子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袅袅婷婷的飘过来,心思忍不住一阵颤动,她一下子喜欢上那女子的身段,女子骑自行车的优雅,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骑上自行车让自己这么优雅的从人群里走过去?
她不想回去,老爹还在骂四姐?
老妈也不吱声,任老爹那么骂?
她没有回家,晃到大队院门口,没有人知道她去大队院门口干嘛,都把眼神儿用到三姐身上了,她即便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居然没人理会,她感觉很爽,她看见大队院里晃来晃去的人影,那一群年轻干部里唯独没有罗震东,罗震东哪里去了呢?
几天不见三姐和罗震东约会了,三姐也不那么叽叽喳喳的说罗震东家里这样好那样美的话题了,刚回来几天那是嘴巴不见闲着,说罗震东老妈可像个当官的,老爹更像个吃国家粮的干部,三姐说的也是实话,罗震东老爸是一个单位的副主任,医院里的大夫,家庭条件可是真的好,三姐去罗家不知道人家爹妈愿意不?这个没有听见三姐说过。
老妈也问过她去罗家,罗家人待她好不?三姐总是绕着弯子没了下文。
杨杏心里为三姐犯嘀咕,如果好的话那三姐肚子连个屁都藏不住的人,为什么不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呢?几天三姐不是很高兴,她也懒得蹭鼻子蹬脸的。
一个有月的夜,三姐出去了,她偷偷的跟出去,她想看看是不是罗震东约她,可出去发现三姐到河边的小树林里一个人背靠一棵树在那里站着不说话,头发像瀑布似的垂落下来,三姐在哭!
她很想上前问三姐怎么回事,又想起罗震东在她心里萦绕的感觉她觉得三姐是罪有应得,城里人怎么会看上乡下人呢?
她又悄悄的从三姐的背后溜走了。
那夜,三姐没有好好睡觉,她也不肯好好的睡下去,她密切听到三姐翻身的动作,她三姐翻一个身来,她也跟着翻一个身来,二姐和四姐睡的像两头猪,还打鼾。
到天亮,三姐都没眨眼。
杨杏的瞌睡跟着三姐的翻身给翻没了。
罗震东回城了,没有带三姐。
三姐自上次跟着罗震东去城里后像变了个人似的,不怎么叽喳了,也不和老爹老妈对着说东说西了,先前总和老爹抬杠,和老妈吵架,现在出奇的不吵不闹了,还跟着老妈和两个姐姐下地干活,回来就爬屋里不出去,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畅快,一顿逮上三碗捞面条现在只是吃那么一碗。
那天她和老爹说想进城,问老爹要钱,老爹乜斜了半天的眼儿掏出一个五块的,她又转过去问老妈要回了五块,十块钱,她算一下够到罗震东家的。
出门走几里路到街上,街上有去城里的车,票车,她上次去时特地记清楚了路怎么走,三姐的记忆真好,走一遍好似走了很多遍的路,她去了。
走的时候,背了一个绿挎包,装了老妈煮的几个鸡蛋,还有在锅里加热的馒头,别的就没有装什么了,三姐走的很安静,老爹没说什么,老妈也没有说什么。
三姐走了。
三姐走后的第七天有人捎信给老爹,要老爹进城去罗家。
老爹那天起个大早,也和三姐一样去街上赶车,捎信的人特地交代老爹怎么坐车,怎么走的,老爹一辈子没有出过老村半步,杨杏那天出奇的跟着老爹一起去的。
老爹不知道要他进城干什么,只说你来就知道了,老爹不忘拿上那杆旱烟袋,烟袋子被灰打磨成明晃晃的样子,老爹的那个旱烟袋用了多少年杨杏不知道,反正记事起老爹都在用那个旱烟袋,车上老爹还不停的摆弄它。
转了一个路又一个路,按照捎信人说的地址找了一天才找上,原来是罗震东的家。
杨杏和她爹敲开一所自建房的大门,开门的显然是罗震东的母亲,和罗震东长的太一样了,她母亲彬彬有礼地把他们父女二人让进屋里,等他们坐下来后,罗震东的父亲从里屋出来寒暄了几句,就是不见罗震东,那老村大队院也有几天没有见到罗震东了。
罗震东的爸爸带着一脸的谦恭给杨杏爹倒茶,拿出糖果,苹果的要他和杨杏吃,杨杏看来看去也不见三姐的影子,她忍不住问罗震东的爸爸:“我三姐呢?”
“闺女,这个,这个,正是要给你们说这事儿呢。”
“我三姐她怎么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她和东儿拌了几句嘴不知道就这么想不开喝农药死了。”
“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她老爹声音颤抖的说道。
“杨大哥,你且息怒,孩子们的事儿不知道咋搞的,吵闹斗气就成这样了,我们做大人的都在上班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事情,东儿回来说谈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谈就谈吧,这不上次就把人给带回来了....”
“一定是你们不愿意我家三妮子才成这样的。”
“我们做老的对他们相处的确没有说过什么的,那是孩子们的事情,管教孩子的婚姻大事那是你们农村有的习惯,城里人对这个没有多少讲究,孩子们能相处我们大人不会说啥子的。”
“那是你孩子变心了,不想要我家闺女了。”
“他们争吵的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天只能对着你们抱歉了,行礼了。”
“你看,是火化还是拉回家呢?”
“我们要震东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不然我们就不拉走人的。”
“东儿现在没有在家,很不好意思,去南方学习了。”
“你们这是骗人!分明是嫌弃俺家闺女是乡下的。”
“如今,我们也只能任由你们说什么了,也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还是愿意给你们一笔赔付金,你看能否商量,如果能商量我们坐下来商量,如果不能商量,那就随便你们折腾。”
“我们就是想要个交代,想知道我闺女怎么死的。”
“这个,我们也无法说的明白。”
“要你娃儿回来!”
“问题是娃儿现在在南方,还回不来。”
“.......”
杨杏看见三姐的尸体是双方僵持了八天谈妥后同意三姐的尸体在城里火化。
老爹哭了,老爹第一次痛彻心扉的嚎啕大哭,骂自己害了三姐,要是严加看管一点,要是知道城里人嫌弃乡下人的道理杜绝三姐和罗震东的来往等等也就没有三姐今天的死。
杨杏和老爹轮流抱着三姐的骨灰从城里回到老村,俩刚刚走到南庄那条银蛇一样的路上,村上的人几乎全围了上来,不亚于大队院里开群众大会的场面:掉泪的,叫骂的,说风凉话的,沉默的村民给杨杏的心头填上一块沉沉的大石头,她抑制不住那种愤怒又向往接踵而来的绝望,一下子把杨杏的精神打入深谷,活泼的,耿直的,率性的,美丽的三姐就这样没了。
她曾经妒恨过的三姐,纠结过和三姐同时爱上的一个男人。
那刻,像老村的残月,萦绕远去。
那刻,像老村南庄的银蛇之路延绵的不知所向,几多迷茫留在她的脑海久久陷入一种无言的境地。
老妈的哭是无声的,她说出一个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按指掐算,三姐肚子里怀娃娃快三个月了,她怕肚子大了衣服盖不住那才叫真的丢大人的,她隐约知道罗震东不想要她了,她怎能咽下这口气,况且你老爹还支持的八万一样,她就想生是你罗家人,死是你罗家鬼,我就是死也要死到你罗家......”
老爹终于还是没有善罢甘休告了罗家,罗震东承认三姐是带着身孕去的,他找各种借口要三姐离开罗家,三姐誓死不迈出罗家半步并要挟罗震东娶她,家人支走罗震东后三姐悲愤难咽服毒自杀,药是她从老村家里带的.....
而罗震东组织上只是免去了他的驻队干部职务调离了老村,听说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过。
谢谢赞赏
赞赏
人赞赏
白癜风治疗医院北京白癜风主治医院- 上一篇文章: 老人中暑昏倒路边超过两小时没人敢扶这事
- 下一篇文章: 这些药物千万别混着服用,会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