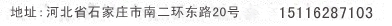方药中辨证论治五步运用举隅
吾师方药中教授从事中医工作四十余年,于中医理论及临床造诣精深。熔四大经典理论于一炉,博采众家,倡气化学说为中医理论渊源,临证以气化学说理论为指导,创辩证论治五步。用之临床,效若桴鼓。值此提高临床疗效为中医工作的当务之急之际,谨举吾师临床医案数例,以为广大中医临床工作者反三。
一.明察标本,以意调之
例一:癫病
韩X,女,31岁
年0月17日初诊:患者五年前因生气突然出现右上肢无力,自主运动障碍,以后反复发作,医院诊为“癫症”,服药无效,发作日趋频繁。最近每天发作两三次不等,发作时四肢失去自主控制,神清,言语不利,且偶有发作性晕厥,跌倒1—2分钟后自行缓解。医院作脑电图检查示“广泛中度异常”,纳佳,二便调,乏力,嗜睡,月经调。诊见患者面色微青,唇有瘀斑,舌体稍大,舌质微红、润,有齿痕和瘀斑,舌苔薄白,诊为癫病小发作。
方老认为:患者病因生气而发,发作时自主运动障碍,且面色微青,身重乏力,据肝在志为怒,主筋,其色青,脾主肌肉、四肢的理论。
步将其定位于肝、脾。其病发作时以四肢运动障碍为特点,且身重乏力,嗜睡,舌胖大有齿痕,脉沉细,证属气虚痰阻,唇舌瘀斑,又为挟瘀象。
第二步将其定为气虚血瘀阻。询其病史,因生气而发病,先见运动障碍,续发乏力嗜睡。
故第三步当定为原发在肝,波及于脾,气虚血瘀在先,痰湿内阻在后。
第四步治病求本,拟疏肝助脾益气养肝祛痰为法。
第五步从脏腑相关理论出发,佐以益肺,取补肺制肝意以助平肝,
因处五味异功散、通窍活血汤、温胆汤合方加减为治:
桃仁10克、红花10克、生姜6克、葱白6克、川穹10克、赤芍15克、菖蒲10克、远志10克、党参15克、苍术10克、茯苓30克、甘草6克、青陈皮各10克、法夏15克、竹茹10克、枳实10克,每日一剂,水煎分两次服,并嘱患者停服其他所有药物。
6月23日复诊:服药七剂,发作明显减轻,一周来共发作五次。乏力、嗜睡亦见好转,舌脉同前。药见显效,治仍宗前,更加黄芪30克、地龙15克以增强益气平肝之力。
7月8日三诊:服药十二剂,发作次数又较前减少一倍,发病时间亦明显缩短,发作症状亦明显减轻,因守原方,嘱其继服,隔日1剂。
9月5日四诊:发作次数减少,两个月来仅发作十次。唇舌瘀斑已退,面色转红润,精神好,乏力、嗜睡基本消失。仍脉沉细,舌胖淡、有齿痕,苔薄白。挟瘀情况已缓解,遂酌减疏肝之品,处十味温胆汤加黄芪、地龙:
法半夏10克、青陈皮各10克、茯苓30克、甘草6克、竹茹10克、枳实10克、菖蒲10克、远志10克、党参15克、生地10克、黄芪10克、地龙15克,水煎分二次服,隔日一剂。
10月7日五诊:服药期间情况稳定,一个月来仅发作两次,最长发作时间达一分钟。继以上方进退调理。至12月23日病人来述,癫病已两月未再发,遍身轻快,诸症悉除,纳佳便调。脉沉细,舌稍淡,舌苔薄白。乃以十味温胆汤加薄荷调理善后,以资巩固。处方:
法夏20克、青陈皮各10克、甘草6克、竹茹10克、枳实10克、党参15克、生地30克、菖蒲10克、远志10克、薄荷3克。
(按〕癫证是一种发作性神志异常的疾病,多由七情失调、先天因素或思它病之后,造成脏腑失调,痰浊阻滞,致气机逆乱,风阳内动所致,而尤以痰作祟关系 。正如朱丹溪所说:“无非痰涎壅带,迷闷心窍”,楼英亦云“病癫者,痰邪逆上也”。方老认为,癫病之作,虽不离乎痰,但此作祟之痰亦不过是致病之标,其本仍是脏腑机能失调。故癫病之治,当以调整脏腑机能为要,治本为主,治标为辅,而于标本之间,谨察其候,以意调之。本例患者,因情志失调,肝失疏泄,致脾气失健,湿郁疾生,痰涎闭窍,发为病疾,本以肝脾气虚而肝病在先,血瘀痰阻为标而痰阻较甚。其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意,标本并举而先以治标为主,待症状控制后又重在治本,以本带标,选方用药得其机要,效果彰著。
二.详辨体质、病时之证,三因制宜
例二:神经性腹痛
郑X男30岁
年12月23日初诊:来诊时主诉三个多月来少腹疼痛,定时发作,每日清晨五时左右疼痛,起床后疼痛自然消失,服中西药治疗无效。除大便干燥,小便稍黄外,余无不适。检其脉弦稍数,舌质稍红、舌苔薄白,诊为“神经性腹痛”。
此患除定时腹痛大便干燥、小便稍黄外无其‘它不适,在分析病情时,方老抓住此息者疼痛皆在每日寅卯交合之时,且起病于秋的特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通于秋和寅时属肺、卯时属大肠的十二辰分属,
首先将其定位于肺、大肠。
第二步再根据青年男性体质多偏阴虚的特点及大便干燥、小便偏黄的表现和脉弦稍数、舌稍红的体征而将其定性为阴虚。考虑病程虽历三月有余,但症状始终如一,
第三步认定其为原发在肺、大肠,证属阴虚。
第四步治病求本,拟养阴清肺润肠为法,因证情较单一,第五步暂未考虑,
处竹叶石膏汤合增液汤方:
法夏15克、南北沙参各15克、二冬各10克、竹叶10克、生石膏30克、甘草6克、玄参10克、生地30克,水煎分两次服,嘱四剂后复诊。
年1月2日复诊:服药四剂,腹痛消失,因公出,未能及时来诊。此间除有两天晨五时左右有轻度腹痛,白天亦觉轻度腹痛外,疼痛基本未再发,二便转调,纳佳便可,脉已不数。病已衰其大半,用药当缓,遂改予清燥救肺汤调理善后。处方:
南北沙参各15克、甘草6克、枇杷叶10克、杏仁10克、生石膏30克、阿胶10克、二冬各10克、桑叶10克、黑芝麻10克、白芍15克
五脏应四时,一日分四时,人体之气与日月相应,又因年龄、性别、居住及禀赋的差异而各具体质特点,治病当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是气化学说的基本观点。此患者以腹痛定时为特点,方老运用辩证论治五步法,依脏腑主时而定位,据病人体质而定性。因时因人而诊而治,方以清肺润肠,无一止痛之药,但药进病止,充分体现了祖国医学三因制宜的整体治疗思想的科学性。
三.全面把握病候,证非仅症
例三:脑血栓后遗症
李XX,女,72岁。
年10月14日初诊:半年前突然出现行路不正,左侧口眼歪斜,医院诊为“脑血栓”,经治疗后上症恢复,但其后一直全身疲乏无力,头晕,哭笑无常,久治不愈。来诊时主诉为头晕疲乏,不欲睁眼,哭笑无常,不能自主。问其食纳尚可,二便调,眠可,无其他不适。检见其脉沉细弱,无明显瘀色,舌苔薄稍黄,诊为中风后遗症。
方老认为,患者半年前突发口眼歪斜,证属中风,病位在肝,但已经治疗恢复,目前仅全身乏力,头晕,不欲睁眼,哭笑无常,说明风证已去而病不在肝。乏力、头晕,五脏虚皆可使然,患者除哭笑无常外无其他明显脏腑症候,故辨证当从情志特点入手,因据肺在志为悲,心在志为喜的理论,
步将其定位于肺、心;
另据乏力头晕、睁眼无力、脉沉细乃属气虚之象,舌明显瘀色又为血瘀之征而第二步定性为气虚血瘀;
又据上述诸症系同肘出现,并无先后关系,故第三步诊其为心肺同病,证属气虚血瘀;
第四步治病求本,拟益肺补心活血为治疗大法;
第五步从脏腑相关理论出发,考虑肺虚不能制木,易致肝旺来侮,还当佐以疏肝法治疗,以助补肺。
因此,总的治疗原则应是益肺补心,疏肝活血,处补中益气汤、生脉散、逍遥散合方,水煎分二次服:
黄芪20克,苍白术各6克,青陈皮各6克,党参10克,柴胡6克,升麻6克,当归10克,甘草3克,天麦冬各10克,五味子6克,丹参15克,鸡血藤15克,赤芍10克,生姜3克,薄荷3克。
85年12月2日二诊:上方服二十剂,头晕明显好转,乏力显著改善,精神已能完全自主控制,情况基本稳定,纳佳,二便调,睡眠好,脉沉细稍弱,舌润稍红,舌苔稍黄。考虑患者已年过七旬肾水亦衰,且瘀血已去,内热之象尚在,当佐以滋肾法治疗,遂去疏肝辛燥2品,加甘寒、咸寒滋肾之药,处补中益气汤、生脉散、增液汤合方;
黄芪20克,苍白术各6克,青陈皮各6克,党参10克,柴胡6克,升麻6克,甘草3克,当归10克,麦冬10克,五味子6克,玄参10克,生地10克,水煎分两次服。
85年12月12日三诊:服前方四剂,药后各症悉除,脉沉细稍弱,舌润,舌苔薄白。嘱患者继服补中益气丸,六味地黄丸以资巩固。每日二次,每次各一丸。
方老认为,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经络定位诊断,除根据症候表现的部位、脏腑各自的功能特点、各脏腑病变的体征特点、各脏腑与病因的关系、各脏腑与季节气候方面的关系等进行定位以外,各脏腑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及与体型、体质、年龄、性别、情志关系和治疗经过等都是脏腑定位所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因素也往往成为定位的主要依据。那种认为一些经现代医学检查患有某些疾病,但又无明显临床症状表现的患者(如某些糖尿病患者仅有血糖升高,尿糖阳性而无不适之症,某些慢性肾病患者仅有蛋白尿而无临床症状等等)无证可辨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是没有真正掌握中医理论,只知以症辩证,不懂中医“证”的基本内涵及其外延的表现。方老认为,“证”,就是证据,就是可以据以诊断疾病的各种因素,包括症状、体征、发病时间、病因及诱因、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禀赋、居处环境、生活习惯、病史、病程及治疗经过等等都属于“证”,临诊当综合分析这些因素,证其属于何脏何腑则治从何脏何腑,证其属于何虚何实则治以何补何泻。此患者仅表现为乏力头晕,哭笑无常,无明显脏腑病变体征,然先据心志为喜,肺志为悲的五脏与情志的关系治从心肺,后据年龄所反映的体质特点辅以治肾,药到病除,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例四:干燥综合症
刘xx,女,50岁。
年6月10日来诊,患者十余年来一直眼干、口干、鼻干、大便干,外院诊为“干燥综合症”,经中西医治疗无效。就诊时息者主诉口干无津,眼干无泪,鼻干无涕,大便干燥,眠差易醒。检见头发斑白,衰老外观,脉沉细稍缓,舌淡苔干,外眼无明显异常,同意外院诊断。
方老认为,患者以口、眼、鼻干燥乏津,大便干结及眠差为主要临床表现,结合患者虽年过七七但月经尚调,虽目干眠差但无其他肝病指征,病不在肝肾可知,因据脾开窍于口,其脉挟咽连舌本,胃脉起于鼻侧,挟鼻入目内眦及脾主运化,藏意,
步将其定位于脾。患者干燥乏津,病程已久,貌似阴虚,但舌淡苔干,脉沉细缓,且久服养阴生津药无效,皆证其干燥非津液之亏,乃气虚不能运化律液使然。
第二步定性当为气虚。分析疾病过程,患者壮年发病,无其他病史及明显诱因,十多年来变化不大,
第三步可以定为其原发在脾,证属气虚。
第四步治病求本,拟健脾为主,佐以养胃。为验证诊断,第五步暂未考虑。
方以加味理中汤:
党参30克,苍白术各15克,干姜6克,甘草6克,天花粉45克,水煎分二次服,嘱四剂后复诊。
6月17日再诊:服药四剂,口干现象有所好转,大使转常,脉沉细小弦,舌稍红然转润。药已中病,乃从第五步治来病考虑,在前补脾养胃的基础上加以养肝滋肾,前方加芍药15克,生地30克,取酸以泻肝,甘寒清肾意,兼制肝肾,以助扶脾。
6月27日三诊:服药八剂各症皆趋好转,口干已不明显,舌脉同前,乃遵“阳得阴助则生化无穷”意,前方去苍术,加扁豆20克,玄参15克,天麦冬各10克,期阴阳并收。
7月14日四诊:各症同前,未见明显进步,脉沉细、舌润、苔薄白,拟方仍以健脾益胃为主,住以制肝,仍以加味理中汤加味:
黄芪30克,党参15克,苍白术各15克,干姜6克,甘草6克,天花粉45克,白芍15克,葛根15克。
7月8日五诊:各症基本消失,纳、眠、便均调,舌淡,边尖稍红,苔薄白,继以前方隔日一剂,以善其后。
12月9日又来诊,述前服药病已痊愈,唯近两侧头痛,耳鸣如蝉,脚畏冷,手畏热,纳一般二便尚调,眠差,脉沉细微弱;舌淡润,苔薄白微粘,考虑其既往为气虚体质,参以现症,证其属肝肾气虚,因拟温补肝肾为治,以桂附地黄汤加味调理,服药而愈。
燥证多属阴亏,单纯阳虚气虚不能化津者较少见,本例患者干燥证十余年,方老在分析病候的基础上,根据病史及既往治疗经过,辨其为脾气虚津失布化,更据加味理中场得效之所证,而立健脾益气泻肝清肾之法,药投效显。后又据多加滋阴之药病情反滞之所证,责其为气虚太甚不胜阴柔,治专以健脾益气,佐以泻肝,得收全功。后患者又发头痛耳鸣,方老又据其症状表现及病人既往气虚及发病时天气寒冷之所证,责之其素体阳虚不足又逢天时之虚而然,仍以温化求本,上病下取,药到病除。亦充分说明了辩证论治,绝不能只着眼于症状和体征,而应综合分析与患者和疾病有关的各种因素,从而确定诊断,立法施治。
四.临证知常达变,谨守病机
例五:浮肿
刘某,女,15岁,学生。
年3月28日初诊:来诊时诉三天前始颜面、下肢及外阴突发水肿,无恶寒发烧,不咳嗽。二便尚调,纳佳,眠可,其他无明显不适。检查见颜面轻度浮肿,下肢及外阴凹陷性浮肿。血检:白细胞/立方毫米,中性53%,淋巴45%。尿检:蛋白极少,白细胞0—1,红细胞0—l,管型(-)。血压:/mmHg。舌润,苔薄白,脉弦细稍数。诊为“浮肿待查。”
中医辨证按五步分析:浮肿突发,无外感表证,且浮肿以下肢和外阴为甚,
步根据脾主运化水湿,为水液代谢的枢纽;肾为水之下源,开窍于二阴的生理特点,将其定位于脾、肾。
患者既无气虚之象,又无外感表证而突发浮肿,显然当责之为气滞水停,故第二步定性为气滞水停。
分析患者病史及表现,水肿突发,病情急,病程短,且未见小便不利,似属脾脏气机阻滞,枢纽失职,水失运布,影响下焦气化使然,故第三步可定为原发在脾,波及于肾,气滞在前,水停在后。
第四步治病求本,当拟脾肾同治而以治脾为主,行气以利水。
第五步从治未病角度出发,考虑脾气盛实,当慎防侮肝,且肝主疏泄,肝脏气机畅达,可促进气血运行,又有助于脾肾气机的通利,故当在治病求本的基础上佐以疏肝,遂拟助脾利膀胱,行气利水,佐以疏肝为治则。
处大橘皮汤加味:
青陈皮各10克,广木香10克,桂技12克,茯苓30克,苍白术各10克,猪苓10克,泽泻10克,滑石30克,甘草6克,益母草30克,白茅根30克,日一剂,分二服。
年4月1日再诊:服药四剂,浮肿完全消退,血压降至/88mHg,尿检:蛋白微量,白细胞0—1,红细胞0-1,无任何不适。嘱前方继服四剂,以资巩固。后随访未再发。
浮肿突发,无脏腑虚衰指证者,多由风邪犯肺,致肺失宣降,水道不调所引起,临床治疗多从宣肺利水入手,肺气得宣则肃降得畅而水道自调,浮肿自消。此例患者,浮肿突发又无明显脏腑病候,抓住其病急起、其证属实、未见表证、病不在肺,且浮肿以腰以下为甚的特点,从脾为水液代谢的枢纽,脾气被郁,气滞水停入手,以助脾行气利水佐以疏肝为治,一药而愈。说明浮肿突发之实证,亦不能拘于风水为患,临证只有既通其常,又达其变,辨证明确,才能效若桴鼓。
例六:支气管哮喘
易某,男,21岁,工人。
年10月19日初诊;来诊时诉咳嗽气喘已逾两月,每于夜晚1~2时因憋气而醒,醒后咳喘发作,发作时张口抬肩、喉中痰鸣。白日活动多时亦偶有发作。外院诊为“支气管哮喘”,治疗不效。问其饮食尚佳,但大便偏溏,小便尚调,睡眠受咳喘影响而较差。检见其舌质红,有齿痕,苔黄,脉沉细弦稍数。
中医辨证按五步分析:
患者病以憋闷咳喘为主,虽肺主气,司呼吸,然肺主呼气,肾主纳气,且其病作每于夜半之时,夜半属肾,故 步将其定位于肺、肾。
患者为青年男性,从体质特点上讲多偏阴虚,事实上其舌红、脉细弦稍数,亦证其恰属阴虚,且其病作每于夜半阴盛之时,亦证其为邪伏阴分,阴气不足,至夜半得天地阴气之助方能奋起抗邪之象;舌苔黄、咳喘憋气、喉中痰鸣又证其蕴有痰热之邪,故第二步定性为阴虚挟痰挟热。
分析病史,起病即见每晚哮喘发作,未见明显诱囚,故第三步定其为肺肾同病、肺肾阴虚挟痰挟热,
第四步治病求本,当以滋补肺肾清热化痰为法。
第五步从治未病的角度出发,肺阴亏虚,当防心气来乘、肝气来侮;肾阴不及,当防脾气来乘、心气来侮而佐以清心、平肝、泻牌的治疗,
然考虑滋肾水即可涵肝木、制心火,化痰湿即所谓泻脾气,故仍拟滋补肺肾清热化痰为治,
处麦味地黄、定喘汤合方:
天麦冬各10克,五味子10克,生地30克,山萸肉10克,山药15克,丹皮10克,茯苓30克,泽泻10克,白果10克,炙麻黄6克,法夏15克,冬花10克,苏子10克,桑白皮10克,杏仁10克,黄芩10克,甘草6克,每日一剂,水煎分二次服。
87年10月22日再诊:服前方四剂,咳喘不作,大便转调,小便,纳、眠均调,仍舌红苔黄、脉弦细稍数。虽邪退病减,但未全除,嘱继服前方。
87年10月26日三诊:前方又进四剂,除10月22日夜间又有轻度喘咳外,哮喘均未再作。纳、眠、便均调,舌红齿痕,苔薄黄,脉沉细稍数。虽痰邪已去,但余热未清,遂去化痰之剂,酌加养阴清肺上品,改予麦味地黄汤、竹叶石膏汤、麻杏石甘汤合方;
天麦冬各10克,五味子10克,生地30克,苍白术各10克,山萸肉10克,木瓜10克,丹皮10克,茯苓30克,泽泻10克,淡竹叶10克,法夏15克,生石膏30克,南沙参15克,甘草6克,大枣10克,麻黄(炙)6克,杏仁10克,水煎分二次服,每日一剂。
87年10月29日四诊:上方又进四剂,咳喘未再发作,全身情况好转,纳、眠、便均调,脉沉细,舌仍偏红,苔薄白。嘱前方继服,隔日一剂。两周后又来诊,情况稳定,未见反复。后以上方合河车大造丸配成丸药,以调理善后,追访至今未再发。
[按]哮喘之病,初病多实,久病多虚。实多是寒痰或热痰壅肺,虚无非是肺气虚卫外不固、脾气虚痰浊内生、肾气虚摄纳失权,且其病以属寒者居多,以阳气虚为本。此例患者,虽病程不长但病作有时,虽大便偏溏但舌红苔黄脉弦细偏数,方药中老师抓住其病作有时正气已虚的关键,根据病人的舌、脉之象及体质特点,一反常法而从阴虚入手,以滋补肺肾之阴为主而收全功,从而提示我们:临证之时当通常法但不拘常法,守病机而巧用变法,才能事半而功倍。
I版权声明:
本文选自:《光明中医》年第3期,作者:高思华。
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信息。本
- 上一篇文章: 江安东城小学公交站一妇女突然晕倒,吓坏路
- 下一篇文章: 渔父记事4高血压病脑出血后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