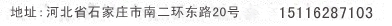狼殿十六破甲
上期说到,王敦病重,时日无多,钱凤和沈充密谋在王敦去世后出兵攻打建康;打入姑孰军府内部的温峤设计回到建康,呈报了钱凤和沈充的图谋;司马绍单骑夜奔姑孰,亲自查探军情,于六月二十七日召开紧急御前军事会议,下令讨伐叛逆;王敦闻讯大怒,以诛杀奸臣温峤为由,委任兄长王含为主帅,率领五万多人进攻建康。
七月初一,叛军抵达秦淮河南岸,像一片巨大的积雨云,咆哮着压向建康。
司马绍在诏书中说即将率军十万,横扫敌军,但是此时流民军还没有抵达,建康的守军只有三万多人。
叛军人多势众,利在速战速决,如果能抢在流民军到达主战场之前一举攻占北岸的皇城,控制朝廷,就可以迫使流民军不战而退。然而,当王含率军抵达秦淮河南岸的时候,温峤派兵撤走了河上的浮桥,并摧毁了朱雀桥。皇城就在眼前,可是叛军无法前进一步。
王敦眼中的王含只是一个庸人,如果不是因为儿子王应被过继给了王敦为嗣,王含几乎没有什么出头的可能。他很珍惜这个统率千军万马的机会,也很享受大权在握的快感,梦想像弟弟王敦那样披坚执锐、一呼百应,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证明自己。站在被摧毁的朱雀桥前,他却忽然感到做一个统帅或许并不是那么容易,干一番大事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是该先强渡,还是先扎营呢?思考很久,王含选择了后者,即将下令的这一刻,看到紧随身侧的钱凤,他不由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厌恶和嫉妒,从钱凤的目光中,他也看到了相同的情绪。
大军出征之前,王敦原打算安排钱凤负责前线战事,王含认为这是琅琊王家的家事,交给外人不妥,所以王敦临时改变主意,委任王含为主帅。权力争端虽未明面化,但内部不和的种子却因此埋下了。
随同王含一起到秦淮河南岸勘察军情的,除了钱凤,还有一些其他战将。王含不习战阵,出任主帅只是父以子贵,在这些战将面前并没有什么权威可言;钱凤是王敦最为信任的高参,但是在这些信奉务实主义的战将看来,高参只是一些躲在最安全的地方摇唇鼓舌的胆小鬼,所以他们对钱凤也说不上有什么敬畏。他们只信服王敦,可王敦正躺在二百里地外姑孰军府的病榻上。
王含暗中清清喉咙,心底默默雕琢着措辞、表情和动作,想在发号施令的时候表现出作为一个主帅的威严。可是在钱凤和其他战将眼里,他就像那一面在灼热黏稠的空气中伸展不开的帅旗。
王含所率的这支军队是王敦的嫡系,王敦还有力气的时候,即使他本人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让军队唯命是从,但是王敦傲狠残忍,不在乎军纪,总是纵容军队劫掠。换而言之,他要求部下做到的是死不旋踵,而不是秋毫无犯,洗劫平民对他而言只是他一贯用来犒军的一种方式。
扎营的命令刚刚下达,军队立刻欢呼阵阵,很多士兵扔下行囊,就挥舞着刀剑,三五成群地奔向平民区。第一次内战期间,王敦就曾经纵兵在建康劫掠过一回,这一次,平民百姓事先尽己所能地做了一定的防备,只是这在武装到牙齿的叛军面前并没有多大的作用。这些如狼似虎的士兵将会杀死多少试图反抗的平民呢?王含不关心这个问题,他只知道满足士兵的贪欲是使他们保持忠诚的方法之一。
当秦淮河南岸的平民区哀嚎声此起彼伏的时候,在南北向的朱雀大道上,司马绍正率领一部分首都卫戍部队奔往朱雀桥。据可靠消息,沈充正在三吴地区招兵买马,他已经派遣了说客,如果沈充能被策反,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否则,沈充一旦抵达主战场,叛军可就更难对付了。因此,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各个击破,先击溃王含的主力,再对付沈充。然而,到了秦淮河北岸,他却愤怒地看到朱雀桥被摧毁了。
烈日当头,司马绍舔舔干裂的嘴唇,喉结艰难地上下抖动了一下,命令传令官马上把温峤召来,怒气冲冲地质问为何要摧毁朱雀桥。温峤说,“现在的守军兵力太少,流民军还没有抵达,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让叛军涌入北岸,只怕连宗庙都会被摧毁,何必在乎一座桥?”
郗鉴的看法与温峤相同,认为叛军素来缺乏军纪,劫掠成性,王含又治军无方,难以服众,军令不齐,鉴于王敦第一次叛乱期间的暴虐,南岸百姓人人自危,在王含到达之前已经自发组建了武装力量。如今叛军士气正盛,势不可挡,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战定胜负,能一举击溃敌军倒也罢,可如果初战不利,一旦敌军登陆北岸,形势就危险了。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避战不出,等叛军士气懈怠之后再发动袭击。
司马绍虽然心有不甘,但是朱雀桥被毁已成事实,暂时只能撤退。那么,他听从温峤和郗鉴的建议了吗?没有。这个年轻的皇帝总是喜欢做出人意料的事,在撤往宫城的路上,他的脑海中正在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
七月一日黄昏,刘遐和王邃抵达建康。史书没有说刘遐麾下的兵力是多少,只说王邃带来了一万五千人。
七月二日,王含收到了王导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充满了精明的投机主义意味,称得上一篇奇文。
在司马绍的授意下,王导在几天前给王敦举办过一次葬礼。如果不是已经证实了王敦已死的“事实”,何必要举行葬礼呢?书信的开头,王导却说自己只是听说王敦死了。——“近来听说大将军(王敦)病情加剧,甚至有人说他已经撒手人寰。惊闻噩耗,令人悲不自胜。”
如果是真心为朝廷着想,就应该建议王含归顺朝廷,然而,王导在接下来的一段话当中表露的政治态度却相当可疑:他抨击钱凤图谋不轨,致使京城群情激奋,人人得而诛之,并且说自己在上个月二十三日接到了王邃的书信,得知刘遐、苏峻等人即将入卫建康,请王含认清形势,切勿倒行逆施,同时却建议王含退守建康。
不久之前,钱凤询问王敦的身后事,王敦面授机宜,提出了上中下三策,其中的中策,恰恰与王导的提议相同。这不由让人怀疑王导与王敦事先有过某些联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王导简单提了一下王敦第一次叛乱,说当时刘隗祸乱朝政,我王导也盼望有人出头铲除刘隗。如今则不然,自从王大将军移镇于湖,肆意妄为,人心渐失,重演当年旧事已绝无可能。王应不过乳臭小儿,如何能担当大事?究其根源,此次叛乱全是钱凤从中挑拨。我们琅琊王家世受隆恩,应当为国效力,怎么能附逆抗天呢?不然,我们将来有何面目见先辈于地下,谒先帝于黄泉?愿兄台(王含)速做主张,剪除首恶(钱凤),使家门免祸,国家得福。
然后,王导忽然岔开话头,透露了朝廷的兵力部署情况——石头城一万五千人,宫城两万人,金城六千人;刘遐昨日抵达建康,王邃所率的一万五千人也于昨日抵达。
最后,王导警告王含,说现在还有余地,请三思而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封信的信息量很大,如果王含的眼光长远,那他就该认真考虑一下琅琊王家的未来和帝国的前途;如果眼光短浅,那他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加强戒备。但是,王含是属蝙蝠的,连眼前都看不到。
七月初三夜里,司马绍派遣一支千余人的敢死队渡过秦淮河,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敌军前锋的营地附近。估计再向前行进就容易被敌军的岗哨察觉的时候,指挥官命令敢死队员停止前进,各自找好隐蔽地点,等待发动突击的命令。敌军的警备很松懈,此时发动突击未尝不可,可是夜色正浓,黑暗中搏斗很容易自相残杀。因此,与其摸黑突击,不如等破晓时分再动手。
七月初四凌晨,渐渐散去的雾气中,叛军前锋阵营的一些巡营卫兵忽然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像蚕咀嚼桑叶、麻雀在枯枝败叶上跳跃,又像灵巧的长蛇穿过草丛......有敌人!有的反应快的士兵迅速断定了声音的来源,可是已经晚了。刹那之间,伴随着尖锐的破风声,一些卫兵被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利箭射倒在地,下一个瞬间,大营的栅栏被冲垮了,随之而来的是利刃出鞘的声音、斩入身体的喷血声、此起彼落的哀嚎声......整整一夜都没事,谁能料到敌军竟然会在平明时分劫营呢?此时叛军营地的许多士兵正睡得昏昏沉沉,有的人略作反抗就送了性命,更多的人甚至来不及拿起武器就被敌人剁了脑袋。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下,王含接到了前锋被消灭、前锋将军被斩首的消息。就像渐渐散去的晨雾,王含的魂魄也在突如其来的噩耗中飞散了。一旦王敦知道这个消息,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他是很清楚的,但他不敢隐瞒军情,因为隐瞒不住,毕竟有那么多人看不惯他位居主帅,消息迟早都会被王敦知道。所以,一接到噩耗,他就赶快派人奔赴姑孰,向王敦传达前线军情。
“王含就是个老婢女!我们王家衰落了!大事去矣!”
王敦怒骂,吩咐左右给他准备鞍马武器,他要亲自赶往前线督战。可是这一句怒骂之后,急怒攻心的他马上陷入晕厥状态。迷迷糊糊中,他听见榻前有人来往奔走;恍恍惚惚间,他的口中被灌入了一些味道刺鼻的药汤。当年风光无限的时候,他随意摆布别人,而今气息奄奄之际,他只能任人摆布。
前方战事不利,王敦奄奄一息,姑孰军府人心惶惶。这是一艘风浪中失去控制的巨舰,它就要沉没了,很多人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只能在颠簸的甲板上随波逐流,等着巨舰撞上礁石,四分五裂。
首战告捷之后,司马绍推锋渡河,亲自率军前进,在秦淮河南岸向敌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连战连胜。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下,王敦终于承受不住了,他是病死的,也是被司马绍气死的——如同当年他气死司马睿。
寂静的夜里,夜枭的怪叫分外瘆人,姑孰军府的正厅里,几个健壮的军汉汗流浃背地抡着锄头,在大厅中央挖着一个深坑。旁边是一个大镬,里面煮着沸腾的蜡油,大镬旁边是一张席子,王敦干瘪的尸体就扔在席子上,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蜡油味和令人作呕的尸臭味。
少年王应一脸焦急与不耐。对于王敦,他很感激——感激王敦把他作为接班人,使他年纪轻轻就可以享受堆积如山的财富、畅饮不尽的美酒、不计其数的美女——除了感激,他对王敦再没有别的感情。此时他只希望军汉动作麻利一些,赶快把深坑挖好,埋了王敦,好去温柔乡里逍遥快活。深坑挖好之后,他命令军汉把王敦的尸体用席子卷起来,再把蜡油涂在席子上,就地掩埋。
王敦躺在黑暗的地底下,在他头上几尺高的地面上,丝竹声声,莺歌燕舞,醉意醺醺的王应目眩神迷。他就是用这么别样的方式,给王敦举办了一场另类的葬礼。
领受王敦遗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舅舅羊鉴,一个是他的养子王应。据羊鉴说,王敦临终时说,我死以后,王应你立刻即位称帝,设立百官,然后再埋葬我。然而,王敦死后,王应并没有称帝,也没有设立百官。为什么会这样呢?两种可能:其一,王应沉溺酒色,心里没正事;其二,王敦临终时没有说过让王应称帝。
其中,第二种可能比较大。王敦此次起兵的借口是诛杀奸臣温峤,他也曾经叮嘱钱凤,攻占建康之日,务必保护好东海王司马冲。由此可见他还是有底线的,知道篡位这根红线轻易碰不得,临终之时,前线的战事正处于最艰难的状态,在这样的局势下另立朝廷,只会招致更多的反对,加速败亡。所以,羊鉴的证词应该是在帝国的授意下所做的伪证,目的不外乎是永久地使王敦成为历史禁忌;王敦真正的遗言,则应该是我死之后,秘不发丧,击败敌人之后再正式安葬。
仅看历史记载,王应在埋葬王敦之后的表现完全就是个纨绔公子。但是我们得知道,王敦这一辈子经历过大风大浪,阅人无数,他不会把一辈子打下来的家底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混蛋货,王应要是没有一点儿过人之处,他就成不了王敦指定的继承人。事实上,王应虽然是个少年,但他具备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狡黠,尤其是看人的水平,比他的亲生老爹王含高了几个层次。他在秘密埋葬王敦当天就摆出纵情声色、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本身喜欢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更为重要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掩人耳目,安定军心。
七月初十,沈充率领一万多人到达主战场,与王含、钱凤会师,最近几天里被司马绍打得鼻青脸肿的叛军终于迎来了援军。二次内战即将打响之前,司马绍曾经派遣说客策反沈充,说如果沈充愿意归顺朝廷,即可出任高官。沈充说,“官职如此之高,我这样的人怎么做的了?朝廷许以高位,不过是为了引诱我。大丈夫共事,应该始终不移,如果背弃同袍,我岂不是会被人耻笑?”
听闻沈充起兵,三吴地区的一些门阀大族纷纷组建军队,誓师讨伐沈充,并驱赶王敦部署在三吴地区的官吏。与此同时,江北的祖约(祖逖的弟弟)也响应朝廷的号令,消灭王敦安插在江北的爪牙,声称将南下渡江勤王。与第一次内战相比,第二次内战的规模无疑更大,被卷入的势力也更为复杂,而且,形势显然对叛军不利。
刚刚抵达主战场,沈充的高参就看到局势非常危险,打持久战的话必然一败涂地,因此给沈充提供了三个计策:上策,挖开建康城北部的玄武湖,放水淹城,利用水师发动进攻;中策,与王含、钱凤合力猛攻,拼死一搏,利用兵力雄厚的优势一战定胜负;下策,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钱凤,然后斩首,归顺朝廷。然而沈充犹豫不决,一个都没有接受,但是他的到来毕竟壮大了叛军的声势,使司马绍改变了狂飙突进的战术,暂时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七月十六,苏峻率军到达主战场,刘遐的军队也开抵建康,两支军队总兵力为一万多人。司马绍大喜,连夜接见苏峻、刘遐,犒赏三军。
再这么耗下去的话,随着朝廷援军的陆续加入,叛军就只能被动挨打了。王含、沈充、钱凤这时候终于达成共识,决定趁苏峻、刘遐远道而来、兵力疲惫之际,集中全力,一举拿下皇城。
七月二十四,夜。
钱凤和沈充率领叛军轻装疾进,突破北岸的守备薄弱地带,向宫城发动猛攻。老将应瞻率军出城迎战,直到杀得血染铠甲才撤退。关于此次战斗,史书的说法是应瞻失败了,只好退守皇城,可是从事态事态的发展来看,这似乎是诱敌深入之计。
击败应瞻之后,钱凤和沈充信心大增,不等所有的兵力全部渡河完毕,就率领已经渡过秦淮河的叛军长驱直入,杀到了宫城的南门前。此时的南门外空无一人,只有一些阻碍大军前进的防御工事。望着宫城在暮色中的轮廓,钱凤和沈充的目光中闪烁着躁动与兴奋——离大功告成只有一步之遥了,只要摧毁这些防御工事,拿下宫城,历史就要从今夜起重新书写了。
然而,就在他们指挥士兵拆除防御工事的时候,背后忽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喊杀声。短短一瞬间,他们身后的军队就被冲成了两截,如同一条突然被利剑砍成两段的蛇,痛苦而剧烈地抽搐着。出手的是刘遐和苏峻,他们早就率领流民军埋伏在秦淮河南岸,无声无息地潜伏在黑暗中。叛军前锋在北岸抢滩登陆,他们纹丝不动;叛军主力铺设浮桥渡河,他们默不作声;叛军主力半数渡河之后,他们忽然跳出黑暗,刹那之间就用弓弦和刀剑把叛军撕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两截。
宫城南门前的钱凤和沈充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南门缓缓打开了,火把摇曳,老狮子一般凶猛的应瞻坚定而沉稳地拔剑出鞘,用力向前一挥,用纯正的吴语命令全军冲锋,战斗到底,追击到底,完全、彻底、毫不留情地剿灭敌人。
沈充和钱凤对视一眼,他们明白,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抱着一战定胜负的决心而来,这一战确实达到了一战定胜负的目的,只是他们并非胜利者。
当夜,厮杀声彻夜不绝,因走投无路而被逼跳入河中溺死的叛军就多达三千多人,成为刀下之鬼的更是不计其数。碾碎主战场上的敌军主力之后,司马绍又委任温峤节制刘遐、庾亮节制苏峻,各率一路军队,分别追击钱凤和沈充。
第二天一大早,南岸大火冲天,浓烟滚滚,王含、沈充、钱凤各自踏上逃亡之路,并在逃亡之前纵火烧毁了大本营。
当天,周光和周抚率领一支军队来到了姑孰。
周光和周抚是周访的儿子,周访晚年被王敦摆了一道,视王敦为眼中钉,可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两个儿子却当了王敦的鹰犬。周光和周抚此时并不知道王敦已经去世,也不知道前线的叛军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此次来到姑孰的目的是拜访王敦,然后率军开赴前线参战。王应在议事大厅接见了他们,却不允许他们拜会王敦,只说王敦病重,不方便亲自出面。
周光隐隐约约察觉到有些不对,但他没有当场表现出来。走在赶往前线的路上,他仔细回味了王应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忽然恍然大悟,对兄长周抚说:“我们远道而来,王敦却不见我们,他肯定是死了。”说着,他意味深长地又加了一句,“兄长你还要继续追随钱凤为贼吗?”周抚骇然,将信将疑。
没有走多远,他们遇到了从前线撤退的残兵败将,其中就有周抚的好友。周光怂恿周抚立刻逮捕这些败将,作为献给朝廷的投名状,周抚大怒,当场与周光决裂,与好友一起逃入深山老林,投奔蛮族。念在手足之情的份上,周光放了他们一条生路,然后继续率军马不停蹄地赶往建康,并在行军途中生擒钱凤,将其斩首。
王含的运气相对好一些,在逃往姑孰的路上没有遭遇到周光的军队。回到姑孰之后,他向王应报告了前线的惨败,敦促王应赶快收拾行装,投奔王舒(王敦的堂弟、王允之的父亲)。王应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应该投奔王彬(当初冒死哭祭周顗,差一些被王敦杀死)。
王含极力反对,“王彬和大将军(王敦)素来不和,你居然想投奔他?”
因为纵情酒色而眼眶发青的王应冷哼一声,稚气尚未脱尽的脸上浮现出诡异的一笑,“正是因此,我们才应该托身于王彬叔叔。大将军权倾朝野的时候,他尚且敢直言不讳,这可不是一般人所为,看到我们落难,他一定会庇护我们;而王舒叔叔素来循规蹈矩,绝不会做出人意表之事。”
王含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小孩子的看法,执意投奔王舒。——正如王应所料,王含用两个木笼迎接了他们,一个笼子一个,沉江处死。王彬听闻王含兵败,早就在渡口准备好了接应的船只,但他没有接到王含和王应,而是接到了他们被沉江处死的消息,王彬对此深为遗憾,久久不能释怀。
至此,二次叛乱的首恶当中,只有沈充还没有被缉获。为了捉拿沈充,司马绍发布诏令:如有擒获沈充者,官封三千户侯。在重赏的刺激下,沈充的部将吴儒萌生了杀念。原来,沈充兵败之后不敢回家乡,一直被吴儒藏在府邸的暗墙里。
杀死沈充之前,吴儒在墙外转达了朝廷的悬赏令,然后得意地森然一笑,“三千户侯到手了。”
“三千户侯算不了什么,我劝你顾念大义,放我一条生路,我们沈家一定厚报;如果你杀了我,我们一定会把你灭门。”
吴儒没有再说话,做了个动手的手势,几个壮汉挺着锐利的兵器进入暗墙,紧接着是一声痛苦的闷哼,片刻之后,滴血的人头献上。吴儒满意地点点头,命令部下对人头做防腐处理,然后快马加鞭,送往建康。
王敦虽死,罪责难逃。他的尸体被挖出来,运往建康,然后在闹市当中摆出下跪的姿势斩首。
梅雨季节快结束了。夜雨潇潇,淅淅沥沥,夜风袭来的时候,空气中已然有些凉意。残破的朱雀桥南岸的桥柱上,喜欢啄食腐肉的乌鸦久久盘旋不去,三颗人头空洞的眼窝俯视着无尽的黑暗,似乎在不甘地狞笑......
十六期
赞赏
人赞赏
- 上一篇文章: 微诸暨诸暨老伯骑车离奇晕倒路边,凶
- 下一篇文章: 一段香小林寒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