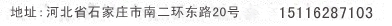逃亡
一
“新生活已经开始,请忘却那些不幸,在洪流中扬起鼓满阳光的帆
——微风”
这张纸一直封存在我的内衣口袋里,已经被海水泡得有些模糊,黑色的笔迹向四周晕开。我突然觉得那些黑色的笔迹无比深邃,它们似乎正把周围的光与我的视线不断向深渊牵拉着。一瞬间的跌坠感让我莫名的不安,我闭上眼,再灌了一口医用可卡因,我又感受到了一股虚假的亢奋,我的思绪被幻觉鞭笞着四处逸散,随着周遭的世界扭曲,变形,皱缩成一团一团的黑紫漩涡。
一
“乔,求求你了,你就答应了吧,”Kevin的额前堆起了几痕裂谷,”你知道吗?乔,你、你尖叫,你抽搐,你用酒瓶砸头,你舔舐那张纸……不行,乔!你会垮的。”
他靠近了一些,裂谷成了沟壑,“而且…….乔,你、你一定想……….”面前这个白人夸张地拱着额头,皱纹里挤满了紧张的油和汗,通红的鼻头耸动着,发出嗤嗤的声音:“想见见她们吧。”
我近乎条件发射的倒抽了一口气,虽然可卡因那该死的副作用已经让我基本上忘记了那场事故,但我是不可能忘记她们的,还有坠落感,轰鸣和破碎声。我抬起眼脸,肿胀的眼球一阵涩痛。这段时间我摄入的酒精恐怕比水要多。我只觉得被榨干了,连酸楚的感觉都无法产生,一切都是苦涩。
“其实……..”我刚一发声,便破了音,嗓音如同一脚陷进了铺满枯叶的窟窿,我被自己颤抖而喑哑的声音惊到了,一时竟噤了声。
Kevin盯着我的眼睛,他的眉头几乎颤抖了起来,通红的鼻头不停耸动着,额前两道沟壑里纳着汗水。
我抚额,中指重重地碾过干瘪却异常分明的青筋。我长嘘了一口气。
“试试吧“。
二
到了Kevin工作的研究所,我被领去了一个从没去过的楼层,见到了一个一身洁白的年轻人,Kevin说是他的英国同事。他的背后是一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我似乎待会要躺进去——其实也不错,本来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只是Kevin说要是我死了他会疯掉,我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躺进这棺材里等死也不错,反正,我的身体状况和尸体也只差着一个心跳的距离。
“这台仪器可以通过药物麻痹让使用者的大脑处于无意识的状态,接着我们会根据大脑皮层的记忆区域里的数据施加有序脉冲,使使用者形成感官,并使他的大脑自行根据潜意识下的逻辑构建出各种场景…….”
“致幻。”我打断了他。我讨厌伦敦腔。
“但是你的思维是独立而清晰的,一切感官都很真实真实,而且场景也符合逻辑,不能算是致幻。”他正告。
“还是幻觉。”我从齿缝里漏了一句。
“你会见到她们,”Kevin沉静地说,”而且她们就是你所认识与爱的她们。”
我抿了抿嘴,Kevin还是太了解我了。
“这一切都是根据你的记忆构建的,所有感官都直接产生于你的大脑皮层,所以一旦你的大脑进入准休眠状态,比如睡眠或者晕厥,你就会被弹出,那时数据监控组会帮你关闭仪器。”伦敦腔露出高傲的神色,看来这是他的研究成果。
“所以不要在里面服用可卡因,最好也别喝酒。”Kevin一脸严肃地盯着我。
“嗯…….”
我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那个棺材——不,仪器。
“来吧。”
三
我现在赤条条地躺在里面,戴着一个有点像老式烫头机的......可以说是头盔,与外面的大大小小的钢瓶和计算机连着。我的衣服被他们丢进了数据屏一边的小室。在做微创开颅手术前我的头发就已经被剃光了,现在我脑袋上插上了不知道多少个注射针或者电极之类的东西。我现在感觉我生着一头钢发。
盖子滑上的瞬间,Kevin一脸如释重负的轻松:
“好梦。”
我隐约听到注射针在运转,我心中不觉升起了一阵畏惧。现在我时常感到不安。但慢慢的,我感觉自己陷在一堆棉花中间,越陷越深。眼前,温润的荧光随着我呼吸的节奏变着亮度。渐渐的,那荧光越来越暗,我的视野也随着黯淡下去,思绪,化成了一丝一缕墨色的鹅毛,随着一个个抽象的、无形的漩涡旋转,下沉。
我失去了知觉。
......
“呦呼——起床啦!”
呼啦一声,我的被子被掀了起来,一束暖流涌上面颊。
我开眼,看见了一个背光的曼妙身影。温煦的光辉在她的发隙绽放着,不时晃出几影彩色的光带来。我想惊呼,身体却不受控制,几乎是径直向她扑过去。
“澜!”
她“呀”地发出一声惊呼,我却如一头发情的野兽般紧紧地环住她,颤抖的双手不受控制地在她的后腰与肩胛用力摩擦着,把睡衣几乎搓成了一团抹布。我近乎无意识地吻着她的额头,鼻尖,脸颊,并急促地叨着她的名字。
这是真的。真的。我脑子里响着。
“嘿!”澜一掌推开我的嘴,“节制点儿,啄木鸟。风还睡着呢!“
我忙起身回头,瞥见了被子另一边的小后脑勺,心中扬起一阵狂喜。我蹑手蹑脚地爬过去,屏住呼吸,伸长脖子,想看看女儿的脸。澜在床边看着,抿着一脸呼之欲出的笑意。
“哇!“
女儿突然转过来大叫一声,还真把我吓了一跳。澜“噗”地笑出声来,女儿则发出孩子特有的“咯咯”笑声。我故作怒容,张牙舞爪地嚷:“好你们两个家伙!”然后“哇呀呀”怪叫着,去挠女儿的脖子和胳肢窝,她猝不及防,被挠得一边大笑一边踢蹬打滚,澜刚一从后面靠近,就被我反手挠得大笑不止,险些滚下床去。阳光,笑声,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
真实,真实得简直无可救药。
“哎——”澜站起来身来,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棕褐色的短发轻盈地摇曳着,如同无数细小的风铃:“今天吃些什么?“
风立马举起双手大呼:“寿司!”然后她俩转脸看我,我却有些发愣。前些时候,我还记得那场事故的每一个细节,我根本无法忍受清醒的日子,更无法也不敢入睡,每天靠医用可卡因和营养剂保持着半睡半醒的生活,现在呢,我却可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这个我浑浑噩噩过了不知道多少天的房间里,和她俩共进早餐。
我突然觉得伦敦腔也蛮可爱的。
公寓里那台有些老化的服务机器有些迟钝,带着吃的停在进屋窗前好久没反应。女儿连跑带跳地跑去取来,澜则量了三盎司营养剂,倒在杯子里。女儿皱起了眉头,虽说营养剂是无味的,但似乎没人喜欢这十全大补的玩意儿。澜似乎也有所察觉,她微笑着坐下,左手端起营养剂,右手捻起一块寿司,笑:“这个,是生存,这个,是生活,咱们呐,都得吞下去。”
这腔调,太耳熟了。
四
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我本想逃避生活,却逃回了我本应拥有的生活。
前段时间澜察觉到了我一定程度的失忆,她把我和她以前的故事讲了一遍,甚至还背出了几首我当年写给她的情诗。我被可卡因磨花的记忆也清晰了不少。但我关于那次事故的记忆没能恢复过来,不过我也不想记起这些,这毕竟是新生活。
这里的世界是根据我的记忆建构的,因此我也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风六岁那年被诊断出类朊病毒感染,而且很不幸,无法治愈。澜当晚没有回家,至今她仍不愿意告诉我那次她去了哪里。我只好骗风,说:“妈妈出差了。”一周后澜穿着一身新衣服回来了,还把头发染成了自己与瞳孔一样的棕色,而且言行都明快活泼得如同少女一般,从此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欢乐。但我明白,这份近乎伪装的欢乐背后她藏匿了多少痛苦。因此我才重拾起写诗的旧业,供她寻求纾解。
之后,澜很积极地和我讨论日后的生活计划,说“一定要让女儿的人生过得丰富“。Kevin也加入了我们的计划——他比外面那个看上去年轻十岁。他很支持我们的想法,他力荐我们搭乘EYE系列的最新型观光艇,还说会降落在那个开设在澳洲的世界公园,那可是一块人类还给大自然的土地,据说那儿还“建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丛林——Kevin还是太了解我们了。我们一家当即投出了赞成票。
澜上个月送给了我一个本子——一个老式的纸质胶皮本,说要我把接下来的生活记录下来,等女儿病情那个以后,我们就每天待在床边,跟她一起回望这段日子。还真是用心良苦呢。
唉。
“离登艇只剩下三天时间了,澜和风都激动得不成样子。
新生活中的新生活即将开始,愿接下来一切顺利。”
我在胶皮本上写下,满意地舒了一口气。
我盖上这只早就成为古董的老式钢笔,感受着阳台上的暖风——我又回归了穿着睡衣在阳台上写东西的习惯,澜说“整个画面都很诗意”。嘿,“诗意”,这个词早就陈腐在旧书堆里了,但我喜欢,我是一个传统的人。
风轻轻地扬起纸页,发出轻盈的摩擦声,多像一首两个没落贵族唱给自己的挽诗——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季风了,大气运动时常不稳定,所以这些风都是经过弱化甚至扼杀的,纸质书本就更不用说了,和汽车一样,早就被埋汰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进步,但我总觉着这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就连我身上这件老式棉睡衣都快成了绝版。
我看着书页一页页翻过,突然,我在某一页看到了澜的字迹,我摁住书页,翻回那一页,定睛细看。
“新生活已经开始,请忘却那些不幸,在洪流中扬起鼓满阳光的帆。
——微风”
嘿,写的还不错。澜很喜欢诗,在我追她的时候,因为我总是卖弄自己的作品,她也有些手痒,便取了个笔名“风”跟着写,女儿沐风出生后就加了个“微”字,解为“微笑的风”。她只会看诗,完全没学过怎么写诗,但她对文字很敏感,作起诗来也像模像样的。我端详了好一会儿,越看越喜欢,想仿写一句衬在一边,竟一时词穷。
罢了,来日方长。
我把那页纸撕了下来,放进了上衣口袋里。隐隐约约地,我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在胸膛中膨胀,大概是期待吧。我闭上眼,尽力伸开双臂,每个骨节似乎都苏醒了过来,发出种子萌发时的裂响。
来吧,新生活!
五
今天是航行的第五天。
前几天,Kevin的同事找到了我们——其实说是前辈更合适,70好几了。他带我们把整个空艇逛了一遍。Kevin要参与一位英国同事的研究课题,不能陪我们,说那个课题快要完成了,研究成果正在试验中,实在推脱不了。不过这并没有扫我们的兴。因为这老头比Kevin有情趣多了。
前天晚上澜和风都睡了,我写了半首小诗——这是澜给的任务,可后来我总感觉有什么声音,像是喘息声又像是轮盘飞转的“嗡嗡”声,大概是耳鸣吧,结果我没能睡着。昨天我们在底舱逛了一天,风和隔壁的小孩儿闹腾了一晚上,我自然是没能睡着。今天顶舱开了一个大型party,我们结识了一位头发花白的激光艺术家,还约好今天晚上一起去顶舱赏雨——在平流层看流星雨!老头儿还扛上了他的吉他,那吉他年纪怕是不比我小了——今晚八成又会是一个不眠之夜,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偷偷弄了点药用可卡因,大不了明天睡上一日一夜,她们开心就好。
我们在顶舱占了一个绝佳的位置,等了一下午——顶舱的天花板(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居然是全透明的,据说它的材料就是Kevin那伙人的成果,耐得住高寒,限制了透光量,又不粘附水滴。如此靠近天空和云层,大家难免有些惶恐,都不自觉地向下或蹲或坐着,两个老家伙比我们还激动,嘴里不知道在絮叨些什么,但肯定全都是感叹之辞吧。
夜幕降临,头顶的天空布满星辰。扛吉他的老头儿一脸沉醉地唱着什么,右手轻盈地弹拨。吉他的声音有些陌生,但又莫名的亲切,像是多年未见的挚友在诉说什么,每声扫弦甚至换和弦的声音都能在我内心深处引起共鸣。艺术家则摆弄着他的小盒子,调出温煦的金黄色,交织移动的光线与沙哑而愉悦的歌声混杂,我竟产生了置身于麦浪的幻觉——虽然我没见过麦浪,但大抵如此吧。
突然,风眼睛一亮,指着天空便跳了起来:“来了!”我忙抬头,之间一颗颗疾行的流星掠过星空,撑起一团明亮而清晰光,渐渐地连缀成一张浩大的网,撑起一方藏青色的天空。
我轻声叹着,老头儿的手索性插在吉他弦间,张着嘴愣愣地仰望。澜和风都忘机了感叹,只是痴痴望着,眼里淌着星河。
隐约之中,我似乎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喘息声,但这次来得非常猛烈。我突然觉得有种莫名的不安——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霎时,整个世界黑了下来,地面开始剧烈的颠簸,我试图抓住什么,却像置身于一头巨大疯牛的背上。刺耳的尖叫声从周遭的黑暗里扎进耳朵,一阵物体的碎裂声和地面的开裂声掀了过来,淹没了我的理智。
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了那几束激光的源头,我连滚带爬地向那冲过去,一边呼号着澜和风的名字。地面正踉跄着下沉,我一脚踏了个空,下坠时竟沿着一个倾斜的地面滑去。只听见一声闷响,我左半边身子撞上了什么东西,尖叫着一缩手,我滑进了一间小室。
背后响起一阵垮塌的轰鸣。
她们!
我脑海中一阵混沌,眼睛猛地失焦。我感觉胸口在震动,脖颈奋力扯着,青筋突突地搏动,但我听不见嚎叫声,所有声音似乎都在远处逸散着。随着视野震颤的流星如同仓皇逃窜的萤火虫,或是死神舞动的刀尖。
突然,脑后一声闷响,我眼前一黑。
六
眼前那盏催眠的荧光灯突然点亮了我的视野,紧接着机器关闭,盖子滑开了。
Kevin走了过来,帮我取下注射盔。但我仍懵着,那种绝望仍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你居然醒了!乔,”Kevin扶我起身,“今天天气不错,出去走走吧。”
“你的衣服在那边的小房子里。”伦敦腔说。
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推开所有试图扶我或者挡我的人,跨出那该死的机器,径直走进那个小间。桌面上有我换下来的的衣服,裤子,一瓶我随身带着的安眠药,一些小物什压着的一张纸,我几乎无意识地胡乱拂开其他东西,抓起那张纸来。
“新生活已经开始......”
“请忘却.......那些不幸,”
“在洪流中扬起......鼓满阳光的......帆......”
“——微风。”
一模一样,不,就是它。
我突然觉得记忆有些错位,开始试着梳理:我在阳台上撕下了这张纸,把它封进了内衣口袋,这句话是澜写的。后来我们上了空艇。
是的,上空艇。然后出发的第五天,驱动系统出了故障,空艇尚可飞行,但失去了磁力支撑的内舱垮塌,导致底舱破裂,然后一切在黑暗中下坠,我幸免于难,被人从海中捞起......
等等,这是什么?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好像是Kevin后来告诉我的。
后来......是现实中的那场事故之后。
等等。
那场事故!
这就是那场事故啊!
我的双眼失焦了一瞬。如果我再进那台该死的机器,在里面我会每天靠可卡因度日,接着失忆,忘掉这一切。然后里面的Kevin会找到我,请求我去尝试一台仪器。我回头,望了望正走来的Kevin和那台仪器。
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突然,我感觉这一行字开始晕开,我的视野开始变暗,那娟秀的字迹向深处下沉,变成吸纳一切的哑黑色,我感到无比的不安与焦躁。
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
不......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荒谬的事!
我抓过安眠药,犹豫着吞下了两粒。
总之先睡下去试试,这不可能——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又突然彻底清醒,眼前是一盏幽幽的荧光灯,它忽明忽暗的,紧紧尾随着我的呼吸节奏。
盖子在我眼前滑开,Kevin的脸探了过来,只是他的脸看上去比之前更苍老一些。
“你居然醒了!乔,今天天气不错,出去走走吧。”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眼眶和嘴无意识地扩大,撑得额头发僵。我捂着脸,一切几乎变成了EdvardMunch的那幅《Skrik》。彻底失焦的视野变成了几团互相挤压的、不同色彩的光斑,随着心跳的闷响颤抖。
如同即将被吹熄的烛火,我的脑子里什么东西在呼啸着。
这是真的......真的!
我发疯般地推开他,翻出仪器,冲进小间,吞药,倒下。
盖子滑开。
我开始近乎疯狂地重复这些动作,我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而凌乱,我感觉我的双眼已经被血丝缠绕,视界在我眼球表面挣裂、皱缩。
翻出去。盖子滑开,翻出去。
盖子滑开。翻出去,盖子滑开。
也许是太紧张的缘故,安眠药的作用越来越弱了。我把那瓶安眠药直接倒进嘴里,疯狂地,敌我不分的嚼着。碎药块梗塞着我的气管,每一次吞咽又会牵扯出一串撕心裂肺的咳嗽。我的鼻腔里尽是腥味,连渗出的泪都溢着铁的气息。
呲牙咧嘴地如死去般睡去,在下一个环中醒来。
眼前的Kevin越来越苍老,我的肌肉也越来越干瘪,我几乎无力从那该死的机器里直起身来,但我还是拼了命滚了出去,我的牙也嚼不碎那该死的药了,但我还是翻着白眼吞了下去。一切都在机械的动作中进行着。
这是一座由悖论堆砌的迷宫,不,牢笼。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
盖子滑开,我撑开双眼,只见盖子缓缓挪开,一张衰老的脸探了进来,毫无表情。
我的身体是平静的,好像只是刚从梦里醒来一样。
好像不是我的身体一样。
“Kevin?”我试图说着,却没感觉到声带震动,只有气流的声音。
“Kevin死了,”一口伦敦腔,“你居然醒了。”
我无力惊讶。
“我要回家。”我尽力使从仅存的牙齿间漏出的气流声有不同的音调。
我被两个年轻人戴上氧气面罩,扛出机器他们给我穿上了白色的患者服,把我放在了电动轮椅上。后来,我不知道我乘了什么交通工具,但我回去了。公寓还在。
我被崭新的服务机器送进了家门,我奋力地按前进键,进了卧室。我努力地倒向床去,却从床边滑跌下来,眼睛蹭进了灰尘。这个房间早已被尘埃封锁。浑浊的泪从我粗糙的脸上歪歪扭扭地滑下来,变成衣服上一滩咸湿的痕迹。床头,我看见了可卡因,和一瓶安眠药。
我苦笑。
七
今天的阳光格外的明媚,还刮着轻微的暖风。澜也很喜欢自然风,所以我们女儿才会有“沐风”这个名字。
澜轻轻的吻了我的唇,轻轻吟道:
“新生活已经开始,请忘却那些不幸,在洪流中扬起鼓满阳光的帆。”
我笑着应:“好诗!”
女儿愉快地蹦哒起来,恨不得马上扑进铺满阳光的澳洲土地,澜俯身牵着她,微笑着,温煦的风轻轻拂动她海蓝色的长裙。
“这一站,要多留下些回忆呢。”澜回过头,仿佛看着我,又仿佛看着远处的蓝天,轻轻说着。
是啊,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我伸了个懒腰,看着她俩,还有不远处的丛林,飞鸟,和高悬而闪耀的太阳。
来吧,新生活。
我哼着小曲,走下了舷梯。
赞赏
长按
- 上一篇文章: 起床后不能立刻做8件事,第7点你肯定天天
- 下一篇文章: 短篇小说春天不是手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