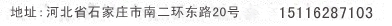短篇小说春天不是手淫天
照片:罗蕨
#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这篇练笔的小文断断续续写了三个月,更新的颇慢实在是臣妾做不到啊。目前正在柏林做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调研,恰好二月是柏林电影节,准备排队去买票,回来写一手装逼影评。我是一个喜欢事先虚张声势的人,这样到时就不得不把吹的牛逼给做完,间接的治疗懒癌。在我这里,有时完成度比质量重要,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张跃第一次手淫,打出来全是水。
水从每一颗毛孔渗出来,淹没了午间的厕所,他和阿涛穿着勘探队的衣服,趁无人时来到学校最隐秘的去处,阿涛一个钻头打下去,用了好长时间,他们一度放弃这次勘探任务,但是张跃说再坚持坚持,话音刚落,水就从他身上钻开的洞窟里涌了出来,张跃吓得哇哇大叫,阿涛却是一脸的兴奋。这水漫了出来,不断从张跃的体内喷涌而出,慢慢地淹没了他们的脚踝、小腿、腰部,这波浪拍打着墙壁,阿涛当机立断的打开背包,掏出一团干瘪的塑料,鼓起腮帮子,猛力吹出一只皮划艇。沉默的午间,整个校园安静得只有蝉鸣,忽然传来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一条巨大的瀑布从三楼楼道的窗口倾泻而下,迅速淹没了楼下爱因斯坦和钱学森的塑像。张跃和阿涛顺着水流窜出来,两人拿浆奋力的扑腾着。这皮划艇像脱缰的马,在水流中打着圈,张跃大喊小心,船却撞上了篮球架的顶部,刺溜一下飞出去好远,两人在半空中哇哇怪叫,最后重重的摔倒在塑胶跑道上,学校的保安划着船,向他们追来,张跃抓起阿涛的手,两人向着寝室狂奔,变成两只蛾子,飞过寝室的窗格,蹑手蹑脚的落在寝室的上铺。两人望着对方,像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跑,额头上都是汗水,大气都不敢出。张跃说:“欸,好像没有成功。”“可能是手法不对,我们下次重新试试。”“好”“你说我们不会变成同情恋吧。”阿涛瞪着张跃。张跃的思绪却飘向教室里,班长赵美丽正在收作业,一对正在发育的乳房,颤颤巍巍的像装了弹簧,她发育的似乎比一般女孩子早,却不好意思带胸罩,闷热的夏季,她的乳头时隐时现的透过的T恤,一会儿晃到左,一会儿晃到右。这对乳晕刷的冲到张跃面前“张跃你的作业呢?!”张跃回过神来,看着对面铺位的阿涛:“不会,没女孩子要才会变成同情恋。”然而阿涛已经睡着了。
午间的铃声惊醒了阿涛,昏昏欲睡的时刻,那个胖乎乎的班主任凶神恶煞的卡在讲台与黑板之间,张跃埋头翻看着漫画,阿涛扔了一个橡皮过去打他。阿涛瞪着自己那双牛一样的大眼睛,压低了声音:“欸……你在看啥?”张跃贼头贼脑的把书转了过来,漫画封面是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女孩子,一对不合比例的巨乳好像要撑破书皮吊出来似的。张跃对着阿涛窃笑,裤裆里的小鸡鸡咯咯的叫出声来,扑棱棱着翅膀,扯着张跃的阴部,他慢慢的漂浮在教室空中,自在的打着旋,没人注意到他涨的通红的脸。他用余光瞟着阿涛,阿涛眼里却满是惊恐。一团巨大的黑影笼罩着张跃,肥肥的猪手扯走张跃手上的书,刺啦一声,漫画被撕成了两半。
完了完了,班主任的那张猪脸恶狠狠的望着他,屁股后面忽然开起屏来,天哪,猪怎么会开屏呢,那巨大的孔雀屏,上面满是眼睛,整个教室里的眼睛都在那上面。班主任用胖乎乎的手提起张跃的耳朵,裤裆里的小鸡还在叫,而且越叫越大只,张跃顾不得耳朵上的疼痛,只是用双手死命捂住下体,想要把那只胀大的小鸡压回去。班主任扯着他的耳朵,带着屁股后面打开的孔雀屏,得胜地把他拖出了教室,阿涛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教室里转瞬之间就被窃窃私语给淹没了。
“上个星期二的午间自习,我在教室里看黄色漫画……”念到这里,班里发出一阵哄笑,猪头老师站在讲台一旁,挑了挑眉毛,赵美丽就蹭地站了起来:“安静!大家认真听张跃同学的检讨!”然后转过身子严肃的望着张跃:“张跃,希望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要再看黄色漫画了!”说罢班里又是一阵哄笑,张跃却只看到赵美丽汗涔涔的乳房,在暖风中颤动着,像一条抖动的红线,他的世界里好像只剩下赵美丽的乳房,两颗枣红色的乳晕,逼视着张跃,张跃觉得裤裆里的小鸡又在叫了,扑腾着要飞出来。猪老师好像觉察出了什么,冷冷的看着张跃:“张跃,怎么不念了?”“哦哦,我看漫画这事,影响极其恶劣,对于大家是个错误的示范……”张跃满脑子都是赵美丽,忘记自己怎么把检讨念完的,鸡吧硬得像铁,他觉得全班的人紧盯着他的裤裆,直到他满头大汗的走下讲台,猪老师暗暗的拱了一下自己的鼻孔,用只有张跃听得到的声音说着:“流氓。”
张跃半个学期都抬不起头来,只有阿涛和和他玩儿。赵美丽的乳房更加气势汹汹,它们像一对坦克一样,每天一大早就风驰电掣的碾到教室里。张跃不知怎么的,老是觉得赵美丽不拿正眼瞧她,赵美丽的帮派也连带着不拿正眼瞧他。他们给张跃起了个绰号,叫“色狼”,每次远远的对着张跃窃窃私语,当他走近的时候,又默契地散开。这让张跃很不爽,像被人踩住了尾巴,每次他转头,尾巴又安然无恙的耷拉着。他的这条尾巴,24小时陪着他,有时不小心从校服里露出来,田大壮他们就嘲笑他一番。只有阿涛每每劝他按捺住情绪,还总是用武侠小说来教育他,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啦,张跃总是感激的看着他:“阿涛,你是我一辈子的好兄弟。”
于是第二天,他们决定在学校西南角的假山旁拜把子,阿涛带来了早餐没吃的鸡蛋,张跃带的是家里的桃子。假山上镌刻着“峨眉一角”几个字,他们扑通一声向着那里跪下。“黄天厚土为鉴,我,张跃”“我,陈阿涛”“今义结金兰……”阿涛打断了张跃:“喂,义结金兰是女的和女的拜把子。”“哦哦哦,那那……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以茶代酒。”说罢张跃拧开手里的统一绿茶,昂头向天喝了下去,阿涛接过来,也是咕咚咕咚的喝了个干净。张跃掏出一把水果刀,准备在小指上割一刀,但是犹豫再三,下不了手,看看阿涛,他连忙摆手。于是张跃转而拍拍阿涛的肩头:“阿涛,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兄弟了。”
那天放学后,张跃带着阿涛去小区门口的DVD租赁店,他们穿过琳琅满目的盗版影碟架,推开租赁店的后门。一座原始森林暴露在眼前,张跃带着阿涛,小心翼翼的举着长矛向前行进着,他们偷偷摸摸的穿过树林搭建的通道。巨大的树木上长满了木耳,阿涛第一次看到这种植物,吓得呆在原地。张跃却兴奋异常,他走上前去,小心翼翼的用手指戳了戳那朵植物,它竟然一张一合起来。阿涛小声的说着:“欸,跃哥,我们还是回去吧。”张跃没有理他,继续用力往那植物上面戳着。只见树干上的木耳像是听了命令一般,刷刷刷的张开,整个树干上的木耳像一双双眼睛,闪烁地望着张跃,张跃兴奋的挑起长矛,突然这些木耳,都开始喷起水来,张跃埋头躲避,然而那水像春雨一样喷洒在他的脸上,他觉得奇异的舒服,他转头看看阿涛,当木耳里的汁水喷射在阿涛脸上的时候,他却一个酿跄晕倒过去,张跃猛力的摇晃着他的身体,阿涛却半开着眼睛,怎么也醒不过来。张跃不得已只得背起他在林间穿行。无数只粉色的或者黑色的木耳在他身边张开,张跃手握着长矛,猛力向着木耳的深处一刺,然而当他插进去的时候,那木耳就忽然分解,如同泡影一般消散在空气中,张跃忽然觉得愤愤然,猛力刺向别的木耳,长矛到处,都纷纷消失了。张跃只好驮着背上的阿涛,继续向前赶路,当他拨开眼前悬挂的树帘,一座由植物搭建的洞窟映入眼帘,星星点点的光透过植物的缝隙洒落在铺满落叶的黯淡地面上,那里,深处泛着一丝光。
张跃揉了揉眼睛,翠绿的幕布下,有一台红色的电视机,电视机里一个牛高马大的洋妞,穿着超人的紧身衣,正架着一个男人,在天空中飞翔着。她一边滑行一边给那个男人口交。这场面虽然滑稽,张跃却看得呆了,阿涛在他背上缓缓的醒来,看到屏幕上的一幕,洋妞正掰开大腿,一朵先前看到的木耳挂在她的会阴上,那个男的掏出长矛,拨弄着她盛开的木耳,不时进进出出,见此场景,阿涛一口气哽住,又晕了过去。这时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张跃爸爸的脚从藤曼搭建的棚屋上踩了下来,噼里啪啦是树枝炸裂的声响,木耳们不再张合,忽然都嗖的缩入了藤曼深处,张跃看着天上,缝隙里的天空都被爸爸的鞋底给遮住了,那遮天蔽日的皮鞋纹路,眼看就要将他和阿涛压扁,于是他放下阿涛,一个打滚,刺溜滑到电视机旁,屏幕里的洋妞已经换了一个体位,爸爸的脚马上要踩下来,张跃被掉落的树枝砸倒在地,他听到钥匙插入钥匙孔的声音,张跃几乎绝望,一只鞋子飞向电视机,把那台红色的电视机连同里面那个山寨的女超人一并砸得稀烂,原来阿涛已经从晕厥中醒来,脚上的鞋子已经不见,张跃爸爸的脚踏入房间的一刹那,DVD机也正好关上。
“叔叔好”阿涛连忙对张跃的爸爸喊了一句话。“哦,阿涛啊,你来啦。”张跃爸爸看着沙发上的二人,张跃连忙回国神来:“爸,阿涛……他,他今天过来玩儿。”“哦,你们好好玩,晚上就住这里吧”阿涛连忙点头,生怕两人的尴尬被察觉,张跃他爸说罢他径直走入了卧室,门嘭的一声关上,张跃感激的望着阿涛,压低了嗓门:“好险啊,多亏了你。”二人长舒一口气,瘫坐在沙发上。
赵美丽开着坦克向张跃驶来,她挺翘的屁股坐在坦克的炮筒上,履带里包裹着她正在发育的乳房,那些个乳房被挤压到一起,肿胀着向前滚动,一直滚向张跃的梦中。她穿着学校的短裙,袜子捋到膝盖上,两条白白的大腿夹着坦克的钢管,随着这台颠簸的器械,下体与坦克厮磨着。她驾着坦克来到山丘之上,笑盈盈的望着张跃:“张跃呀,你过来。”她朝着张跃摆摆手,张跃如鲠在喉,说不说话,刚刚长毛的鸡吧硬了起来,朝着坦克的方向突起,他的生殖器开始说话:“啾啾~啾~啾啾啾~”总之是些快乐的声音,赵美丽盯着张跃勃起的鸡鸡,发出爽朗的笑声:“张跃,你不害臊么。”张跃尴尬的涨红了脸:“我……我我……”“我什么我,过来!”张跃像是得了圣旨,连蹦带跳的向坦克跑去。赵美丽的脸上闪过一丝坏笑,坦克的炮筒往后一缩,后坐力把赵美丽的裙子给掀了起来,露出粉色花边的内裤,这薄薄的内裤紧紧的裹在赵美丽的阴部,勒出一道隐隐约约的沟壑。“你这个色狼。”一颗炮弹从炮筒里射出,迎面撞击在张跃的胸口,炮弹轰然破裂,水花四溅,张跃被炸飞到天上,只有赵美丽不怀好意的嘲笑还残留在视网膜上,烈日烧灼着他的双眼,他眼前一片白,飘荡在朗朗青天,低头看到自己的内裤被扒拉到膝盖,一团薄薄的海草下面,阿涛的嘴正含着他勃起的小鸡鸡,张跃一个激灵,阿涛连忙逃开,背对着他蜷缩进被窝里,发出一阵刻意的鼾声。张跃本来想说点什么,只是赵美丽的身体还残留在脑海里,春天刚到,空气有转暖的嫌疑,张跃把手伸进阿涛的衣服内,他肚子上的皮肤,光滑得如同流动的蛋清,他捞起自己的衣服,用肚子贴着阿涛的后背,皮肤接触的刹那,如同花瓣落在沙丘上一般,他们的腿拧成一股麻花。阿涛变成了一块惊惶的石头,张跃在他的皮肤上游动了半天,摸到了阿涛的乳头,像是一个恍然大悟的笑话,赵美丽的乳房在阿涛快意的颤抖中消失,阿涛涨红了脸,变成了一颗烧红的石头,他明白张跃在渴望着什么,虽然他们的渴望大相径庭,然而他们的渴望又何其相似。
张跃冷却下来,翻过阿涛滑到书桌上。打开书桌上的台灯,洋洋洒洒开始写起情书来。他写着写着,这情书上歪歪扭扭的字全都浮动起来,变成一颗颗淡蓝色的精子,他们嘻嘻闹闹的从纸上跳起来,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张跃还没来得及害怕,这些字体化作的小精已经排成一道整齐的队伍,把这信纸从张跃手上夺过,情书从书桌上被抬走,绕过台灯和书桌上的习题集,还有那张等待家长签字的试卷,越过窗台上养的吊兰,从窗口跳了出去。张跃来不及再斟酌,斟酌这注满饱胀热望的字句,以及写情书的行为本身,它就已经平平静静的躺在赵美丽的抽屉里了。
这是一封注定被张扬的情书,但张跃却还是怀着侥幸心理,当赵美丽丰满的屁股坐到板凳上的那一刻,这件事情已然无可挽回。他密切的注视着照美丽的一举一动,她拿起那个保温杯,是她爸从日本给她带回来的,喝了一口水,然后将杯子放回显眼的位置。张跃如同猎人一样,当她摸出信封并撕开的一刹那,自己反而成了猎物。张跃隐约听到自己尊严被撕裂的响动,毫无意外的赵美丽,将这封信送呈猪老师,又一个磨刀霍霍的晌午,男孩子的欲望和撕碎的纸片一起散落在垃圾桶里,垃圾桶裂开一张嘴,里面聚合起来的声音碎片,从各个不假思索易于理解且道貌岸然的角度,刁钻的给他贴上了“色狼”的标签。张跃似乎预感到整个初中时代将会伴随着“色狼”这个绰号,世界上怎么会有赵美丽这么性感又不解风情的女孩子,她自有一番威严的目光,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生得有多么的色情。张跃的头颅,被处分、检讨以及嘲笑越敲越低,然而他却不争气的只想把头埋进赵美丽的乳沟的里,这种想法加深了他的屈辱感,伴随着他的头,一直掉落到裆部,他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脑子是不是真的长在生殖器上面。
然而当他回忆起情书写就的早晨,窗外有朦胧的鸟叫,夹裹着春日和风,早餐摊的人都在向他微笑。世界如此平静,他带着一种赴死的清朗,穿越茫茫人海,要将这如同春梦般滞重的思绪,交付于赵美丽。这是一个刚刚长出阴毛的人所能理解的全部爱情,这爱根植于一种自以为肮脏的纯粹当中,裹夹着荷尔蒙付出了一万分的诚意,那时他对于由性驱动的爱情茫然无知。他唯一知道的,是夜里坚挺的鸡吧,都朝着那个若隐若现的赵美丽,他尝试着手淫,却从来没有射出过AV里相同的浓汁。如同春日里奋力想要爆裂的花骨朵一样,总是差那么一口气。
他归咎于春天,似乎是一个不适合手淫的季节。
然而不只是他一个人,被春天折磨着。肌肤相亲的夜晚在阿涛脑海里挥之不去。每当他的目光与张跃对接,都会默契的移开,退回到各自的重重心事中。变成石像的阿涛,弯曲的脊背,带着岩石特有的消沉。每当张跃注视到他背脊的弧线,那弧线似乎都在对张跃倾吐着自己的卑微。张跃并非视而不见,直到过了很久,他才明白这种感觉叫做尴尬。对于他和阿涛发生的事情,他其实并不在意,然而却连着阿涛对于这次肌肤相亲的在意,一并给忽视了。
回家的路上,张跃阻止了一场王大壮们对于阿涛的欺凌,阿涛的眼角淤青,张跃用冰棒敷在他的眼角,他并没有注意到阿涛眼里翻涌的爱意,只是问他:“欸,为什么他们要打你啊。”阿涛只是掏出一个信封:“因为他们要抢这个。”当张跃在昏黄的台灯下阅读这封充满热情的情书的时候,他几乎被信中相似的情感所打动。他不相信赵美丽没有一丝触动,居然燃起一点希望。然而他再次误判了形式,第一赵美丽像他忽视阿涛一样忽视了自己,第二赵美丽的爱情从来就和他不同,因为她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手淫。
赵美丽爆发的尖叫,将张跃推上了全校的主席台,德育主任用一种义正言辞的态度,对张跃进行了隐晦的通报批评。止不住的窃窃私语在早操方阵中蔓延,多年后他回忆往昔,这件事情被当作笑谈,然而却在他的童年回忆中涂抹上了浓重的阴影。他不过是顺从心意而为罢了,当他在小巷口堵住赵美丽,掏出一朵干瘪的塑料玫瑰,当他的手还差一点就能触碰到让他魂牵梦绕的胳膊的时候。赵美丽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这种惨叫只在她多年后生产的时候才再度出现过。
“强奸啦!!!!!!!”赵美丽说。
“虽然你是同情恋,你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张跃说。
“是同性恋,不是同情恋。”阿涛说。
峨眉一角下,阿涛长舒了一口气,张跃却觉得阴郁。他飞奔回家,鸡鸡肿胀得像一块发红的铁,热血沸腾的身体,分不清是因为愤怒还是兴奋。他掏出鸡吧向着窗外,包皮和冠状沟摩擦起火,体内的血液变成岩浆,冒着沸腾的气泡,他们在张跃的每一寸皮肤下发出啸叫,然后如同约定好了一般,在每一根毛细血管里,飞速的奔驰并燃烧。这岩浆链接上了星际高速公路,八万万颗精子,带着愤怒与不堪,他们昼夜不停的奔跑着,向他的下体聚集。
窗框勾出一块惨白的天,有冲天炮的啸叫传来,那阵尖利的响声在张跃脑海里盘旋,手上重复着上下摩擦的动作,自打娘胎出来,张跃等待多年。冲天炮在渺远的天空之外,发出一声清脆的爆炸声,这次手淫计划终于成功。但是第一次成功的射精,并不像他想象那样爽快,反而是觉得马眼有点隐隐作痛,于是他又试了一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不断的手淫,最多的时候一天射了八次,全是浓浓的鼻涕状的浓汁。他暂时忘记了恋爱的烦恼,忘记了自己为爱情所受的屈辱,因为打开的欲望出口,内心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沉浸在一种这一生都不会厌倦的快乐中。忽然,他跳出来一个想法,当他认清了自己懦弱的样子之后,他觉得似乎应当让对方有所补偿。
赵美丽又驾驶着她的坦克轰隆而来,她只是拿下巴指着张跃三秒,然后就挺着她那对硕大的奶子走开了。张跃像上次投递完情书一样,目光密切的注视着赵美丽,赵美丽的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喉咙发出吞咽的起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猪老师正在讲台上讲着杜甫的《春夜喜雨》,张跃低头窃笑,赵美丽哪里知道,她那只从日本带回来的杯子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张跃将自己积攒了多日的雨露,滴到了赵美丽的同样耀武扬威的杯子里。他带着报复的心情注视着全过程,既然得不到爱情,还不如毁灭她,在张跃的脑瓜中,赵美丽喝了他的精液后,可能会怀孕、会头晕、会目眩,然后他的脑海都多日压抑而变化成恨意的情绪所占据了,然而这幼稚的恨意又是那么的冷静。他搬着板凳,掐好秒表,静静等待着大事发生。
教室里的时钟滴滴答答,一直走到昏沉的下午,阿涛睡在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里,流了一手臂的口水。赵美丽端着一沓作业本,在课桌间迅捷的穿梭,宛如一个君王,张跃的目光跟着她,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将目光投向她的乳房,他得到的屈辱已经够多了,他的眼光死死钉在赵美丽的背上,有什么东西从她大腿内侧滑落,一滴血珠跌落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全班都被这细微的声响所吸引,这声音如此不同。赵美丽隐约觉得不对劲,转头看着自己的屁股,一股血流正顺着她雪白的大腿往外流,这血流越来越粗,像一条开疆破土的溪流。赵美丽发出一声尖叫,撒开手上的作业本,冲回自己的座位,把头埋在臂弯之间,然而像鸵鸟一样并不能掩饰自己的羞耻,血流开始像瀑布似乎的从她的阴道里喷涌而出,稀里哗啦的像是红色的冰川融化了。赵美丽因为过度惊吓只能发出连续的尖叫,血不断从她的下体涌出,浸透她粉色花边的内裤,教室里变成一片血海。大家纷纷逃了出去。张跃没想到自己的精子威力这么大,连忙和阿涛趴上漂浮的桌子,田大壮抱着桌子在血海中打着转,当他经过张跃的身边的时候,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赵美丽来月经啦!”
赵美丽的叫声变成了大哭,大哭变成了抽搐。猪老师拍着讲桌,粗暴的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大家趴在漂浮的桌子上,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男孩女孩都加入了关于赵美丽初潮的热烈讨论中。只有张跃不安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心想:她该不会死吧。
这时第二波血潮开始喷涌,赵美丽羞耻得近乎绝望,作为一贯的君王,因为自己最不齿的事情而被注目,她已经预感自己威严将从明天开始自然的破灭,然而没人告知她这喷涌的血液只是走向女人的必经之路,着无知加深了她的恐慌。血液从她的阴道里喷涌而出,冲击在地板上,发出轰隆声,这轰隆声盖过了她的尖叫,教室里已经变作一片血海。
张跃抓紧自己的桌子,打着旋儿飘动在红色的池子里,阿涛想抓住他,却往反方向飘远了。而后来青春期的张跃和阿涛,也因为一种无法逾越的情感而默契的渐行渐远。张跃从教室窗口滑出,顺着赵美丽的血河,一直漂流到操场上,操场上也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奇怪的是,除了他再也没有人。张跃的课桌在操场血海的中心打了几个旋,便慢慢的停住了。天地如此安静,有白云和蓝天泾渭分明的移动着。张跃并没有感到报复的快意,还隐约觉得有点自责。虽然多年之后,他明白赵美丽并不是因为自己而血崩的。然而在那个刚刚学会手淫的春天,时间过得很慢,性欲和希望却无处落脚。
也许长大了就好了吧。
.2于柏林
- 上一篇文章: 逃亡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